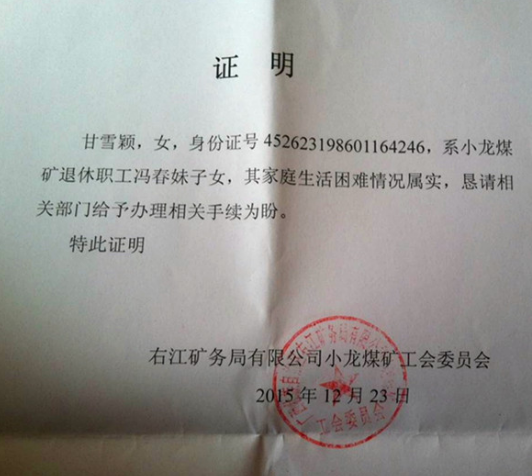范文一:浅谈李杨的爱情故事
浅谈李杨的爱情故事
Tiny 0802
李杨之间爱情的有否,一直都是人们争议与探寻的命题。爱情,两个美好的字眼,如何存在于佳丽三千、粉黛后宫的君主帝王身上?又如何体现于利用妹妹进献争宠的妃子身上?然而,在我看来,李杨之间,是有着纯真爱情的。他们对对方的欣赏、依恋与爱,亦是一段经典、震撼的浪漫。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一个恨字,憾意自是明了。李隆基恨,恨因美人误江山。但更浓烈的,是心中那份因江山杀美人的恨,是生死不见两茫茫的恨。“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足以传达两人之间的情谊。白朴的《梧桐雨》中,“位纵在神仙列,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转情难灭。”是杨玉环对唐玄宗的忆与念;而《长生殿》中,“妃子呵,常记得千秋节华清宫宴乐,七夕会长生殿乞巧。誓愿学连理枝比翼鸟,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命夭! 寡人越看越添伤感,怎生是好! ”则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怀与想。爱,不贵亲密,而贵长久。我想若是梦已成梦,若是回忆已成回忆,若是这份依恋在离别在失去后也随之消散,李杨之间的悲剧,也不至于如此般令人扼腕。
只是这种爱情,生不逢时。
封建传统时代的束缚,年龄伦理上的限制,帝王妃子身份上的禁锢。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诸多阻碍,使他们的爱情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畸形化而过早夭折了。安史之乱的罪名竟落在了杨玉环的身上,所谓红颜祸水,也便是这般形成。即便是挚爱,但唐玄宗肩负的是一国重担啊!他爱她,却爱的无能为力。马嵬坡前的诀别,“一朝红颜为君尽”,使得玄宗的残年注定是要在对杨贵妃的无尽思念中度过。
他们相知相悦,他们亦海誓山盟。他们之间的爱情,在歌舞盈溢中,在诗词吟咏中,在花月共赏中,潺湲熠熠。唐玄宗与杨玉环,天之骄子与一代佳人,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不得不慨叹,人生若只如初见。
范文二: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中的爱情故事 17
前一阶段,我们讲过了白居易的讽喻诗,对于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诗人来说,仅只讲到了很小的一部分。白诗流传到现在的三千首以上,是唐人中最多的。分析起来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本来创作就多。五六岁就开始作诗,现存诗中最早的是十五六岁时的作品,除了大家熟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外,还有象“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等等。他又很长寿,会昌六年“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他就是这年去世的,写诗写了70年。第二,是白居易很注意整理保存自己的诗,据统计先后曾经十一次亲自编辑。最早的一次是贬江州司马以后,他45岁时编成15卷800首,《与元九书》就是这次编成之后写给好朋友元稹的信;最晚的一次是他去世前一年,会昌五年,编成75卷3840首。第三条原因最重要,人们喜欢他的诗。元稹说白居易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对此既得意又不满:“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似乎《长恨歌》在白居易“所轻”之列,是这样吗?依我看,拿《长恨歌》这唯一标出题目的诗做“所轻”的例子,本身就说明不轻。如果一个人,在编完800首之后写了一封信,信中三次提到其中的一首,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一定是对这一首情有独钟,《与元九书》就是三次提到了《长恨歌》。如果一个人,35岁写了一首诗,到74岁还在推敲修改其中个别的字句,我们就可以想象这首诗在他心中的位置,白居易对他的《长恨歌》,就是如此。日本有一部著名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成书于11世纪初,其中引用了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长恨歌》,有两处句子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翡翠衾寒谁与共”和“唯将旧物表深情”在《源氏物语》中分别是“旧枕故衾谁与共”、“空持旧物表深情”。日本著名学者丸山清子经过严密考证,得出结论说《源氏物语》中引用的《长恨歌》,出于会昌二年编定的《白氏长庆集》七十卷本,就是这一版本的《长恨歌》传入了日本,目前我们读的《长恨歌》出于会昌五年编定的七十五卷本。这就是说,在白居易71岁的时候,他的《长恨歌》中这两句还是“旧枕故衾谁与共”、“空持旧物表深情”,74岁时改为“翡翠衾寒谁与共”、“唯将旧物表深情”,一年零三个月后,诗人辞世。
《长恨歌》,白居易是如此地钟爱,当时的人们是那么的喜欢,而且传到了日本,被引进了《源氏物语》,这就说到唐代以后的了,因为《源氏物语》成书时,在中国已经是北宋。那我们就接着说从白居易之后直到今天,人们是怎样地喜爱《长恨歌》:元代大戏曲家白朴根据它写了杂剧《梧桐雨》,清代大戏曲家洪升根据它写了传奇《长生殿》,这两出戏当年演出时的轰动,记载很多,不多介绍,只讲一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曾把洪升请到江宁织造府,连续三天上演《长生殿》,大宴江南江北名流。再引一则2007年1月14日发自布鲁塞尔的报导:“舞台上,唐明皇与杨贵妃重逢四目相视;舞台下,来自比利时、荷兰、德意志、法兰西的近千名观众屏气凝神,剧场内气氛瞬间凝固;待到李、杨二人相拥而泣,全场爆出长达数分钟的热烈掌声,很多人泪流满面……”,这是比利时列日皇家剧院昆曲《长生殿》的访问演出。
《长恨歌》诞生到今天, 1200多年了,为什么1200年来,不但经久不衰,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地,感动着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阶级、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观念信仰的所有人群?它的魅力到底在哪?对这个问题,无数的专家学者,曾经做出无数的答案,但综括起来无非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艺术研究,一方面是主题探讨。
从艺术成就角度论述,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赵翼《瓯北诗话》:“《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辞,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今天大学文科教材这样分析:“情节曲折多变,描写细致,委婉情深,首尾完整,语言流畅清丽,音韵匀称和美,抒情气氛十分浓厚,诗中很少用典,佳句极多。”这些论述和分析,都是正确的;尤其论及很少用典、通俗易懂而又雅俗共赏,确实揭示出了它的读者群社会层面如此之广如此之高下不等的原因。但是以此来回答刚才的问题,显然不够。“语言流畅清丽,音韵匀称和美”,可以使从古到今的汉族读者如醉如痴,但它感动不了外国人。
关于主题的探讨,那就太多太多了,而且历来说法不一,分歧很大,大致三派,“讽谕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至今没有完全一致无可质疑的结论。咱们这个课程从来不参与争论,这里只介绍现行大学文科基础教科书当中的观点,这应该是今人权威性的结论,或者说比较起来得到稍多一些认同的结论:
“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上面的引文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现行大学文科的基础课基本这样讲,关于古代文学普及性文章也基本这样写,大同小异,都是说双重主题,现在被多数人所接受。
对于这则引文,我只提一点疑问:把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之语,说成是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论据是否可靠?我们读通行本《长恨歌》,一般都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它的最末一段是: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
这肯定不是陈鸿《长恨歌传》的原文。“有《玄宗本纪》在”,从这一句,就能判定后人篡改过。唐以后的朝代修唐史,才出现所谓《玄宗本纪》,唐朝没灭亡,历代皇帝只有《实录》、《政要》,不会有《本纪》,中唐时期的陈鸿怎么可能说出“有《玄宗本纪》在”呢?
说后人篡改了陈鸿《长恨歌传》,还有证据,不多论了。从汪辟疆先生辑录的《唐人小说》中可知《长恨歌传》另有一个版本,很多地方跟我们读的通行本不一样,这另外的版本应该是陈鸿《长恨歌传》的原文。它的最末一段是: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居易尉于盩厔,予与琅琊王质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携手入山。质夫于道中语及是。白乐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
这里根本没有“欲惩尤物,窒乱阶”,陈鸿认为他的朋友白居易是因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应该是这个更确实符合诗人写《长恨歌》的本意。
奇怪的是现在很多论者还是引用被篡改的《长恨歌传》,能得到可靠的论据吗?
至于说也有“讽喻”的意味,不如说有“讽刺”意味。“讽喻”是一种规劝,既然白居易没有规劝谁的意思,那么“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等等,尽管讽刺意味很明显,但也不含告戒的意图,那就无所谓是否贯穿到底,无所谓双重主题彼此纠缠了。
“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不但所有教科书这样写,凡是论及《长恨歌》的,其他方面众说纷纭,这点上完全一致。只是为什么同情,同情到什么程度,则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谈而未尽;为什么感动了古今中外所有人群、它的魅力到底何在问题,答案很多,莫衷一是。我们就讲别人没谈或没谈尽的,再加上一条答案。
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开始,《长恨歌》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用了大量凄凉孤寂的氛围描写和波澜起伏的情节架构,反复地渲染李隆基杨玉环二人的生死相恋、魂牵梦绕,同情笔触,在在都是,引述分析的文字非常之多,我不重复。有论者说:“诗最后虚无飘渺的仙境,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了一段神话,给现实的悲剧加了个理想化的喜剧结局,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诗人希望发生的事情”,依我看,与其说是“诗人希望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诗人相信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换句话来说,白居易是以一种看似浪漫主义的手法,似乎是描述虚无飘渺的仙境,而实际上是透露他所知道的并且深信不疑的一段隐情。
远在“虚无飘渺的仙境”之前,长诗行文不到一半的时候,诗人写出了这样四句:
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这四句,多少代的读者从来是一掠而过,没有给予特别注意,直到上个世纪的1929年,一位大国学家突然发现:“夫仅言马嵬坡下不见玉颜,似通常凭吊口气,今言泥土中不见玉颜,是尸竟乌有矣,可怪孰甚焉?”这位国学家是俞平伯,人说他第一个读懂了《长恨歌》。俞平伯分析,这实际是指太上皇已经回到长安后,密令给杨贵妃改葬,却发现没有尸体。新、旧唐书的记载可以印证,俞平伯分析正确,现在学界也基本认同。至于后来又有中国的日本的学者考证说杨玉环东渡日本了,这个不在我们课程研究讲述的范围之内。我们只是从“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两句出发,到以下的诗句去探讨去寻找,白居易认为玉颜到底哪里去了。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天上没有,地底下也没有,那就在地面上吗,“两处茫茫皆不见”,那就在第三处吗,白居易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排除法。按古人认识,人死后,或者上天(碧落)成神成仙,或者入地(黄泉)成鬼,“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那就是告诉读者,杨玉环既没成神成仙,也没成鬼,那她就还是个人,没死。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啊?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忽闻海上有仙山”,闻,听说,那就就必然有人说。谁说?是道士说吗?绝对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他们没找着,说什么啊?最关键的一句话“雪肤花貌参差是”,这里的是,不是现代汉语里是不是的是,而是代词,这、那;“雪一般的皮肤花一样的容貌,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四川临邛的道士见过杨玉环吗?知道她原来是什么样吗?能够向已经被软禁的太上皇李隆基通报消息,而且能说出“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的人,只可能是李隆基多年的亲信。那么这六句诗实际是隐藏了这么一件事:李隆基的亲信偷偷向他汇报,贵妃还活着,我看见了。观众朋友可能注意到了,我对这六句仍然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一步一步推出唯一必然的结论,只可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其他。我的推理过程有毛病吗?
下边我仍然采用纯客观的推理,不带任何主观的感情色彩。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这就是很多论者所说的,“虚无飘渺的仙境”、“浪漫主义的神话”、“理想化的喜剧结局”。平心而论,这一段真是太赏心悦目了,令人神荡魂摇,叹为观止,“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简直美到了极致,美到了无以复加。我真想停止枯燥的推论,好好欣赏一番这虚无飘渺的仙境和浪漫主义的神话,可是“犹似霓裳羽衣舞”一句又把我拉回到形式逻辑的推理判断:这位汉家天子使曾经看过杨贵妃跳霓裳羽衣舞,否则“犹似”二字从何而来?那么,这位汉家天子使更不会是道士,更应该是太上皇的亲信,甚至是心腹。但是,两个版本的《长恨歌传》都说是道士,所有解释鉴赏《长恨歌》的文章也都说是道士,那我不管,我只管细抠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原文,只管按必然的逻辑去推论。在《长恨歌》里,“两处茫茫皆不见”之后,就再也没有道士什么事。这里写的是堂堂皇皇的“汉家天子使”,那就一定是太上皇特派,一定负有重大使命,不派心腹派道士,合情理吗?至于是什么使命,首先肯定绝不是为了取回一股金钗半扇盒,堂堂汉家天子使,万里迢迢漂洋过海,只为干这个,不象话。那到底是什么使命?就在句中藏着呢:“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这明显是答复之词,如果没有相见的邀请,何来“天上人间会相见”这样实际是婉言谢绝的答复?这一大段看似非常美丽的神话背后,隐藏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李隆基派人转达重新团聚的要求,而杨玉环推脱婉绝了。从“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的急切和“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的深情推断,婉绝只能是因为客观形势所迫的不得已。这样读来,结局是喜剧吗?于是全诗的最后四句就很好理解了: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李隆基和杨玉环曾经共同立誓生生世世为夫妻,相爱得是那么深,是那么样的不可分,但他们的命运却被这样安排:先要经历马嵬坡下的死别,后要忍受天各一方的生离!当初死别的时候,“君王掩面救不得”,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现在的生离也同样是迫不得已,不是不愿相聚,而是不能相聚。
最后得强调,以上所讲的不是探讨杨贵妃死没死,那不是拿几句诗就能研究的。我所讲的是白居易当时可能实指什么或怎样设想。换句话说,与其认为白居易编了段神话,不如认为白居易讲了一段实情或者编了一段故事,什么实情?什么故事?没死。没死也不能相聚!
古今中外有多少诗人歌颂过爱情,在他们的诗中,爱情是那么美丽,那么纯洁,能给相爱的人无穷的力量,能让暗淡的世界充满阳光,诗人们把各民族语言中一切美好的词汇,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形象,都赋予了爱情。而白居易笔下的爱情,却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无奈,在外部强力面前是这样的悲苦和可怜;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恰恰就是如此,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也不论相爱者属于哪个阶级尊崇什么信仰。所以《长恨歌》唱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比天还长比地还久的共同的遗憾。
07.04.27.
范文三:论《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