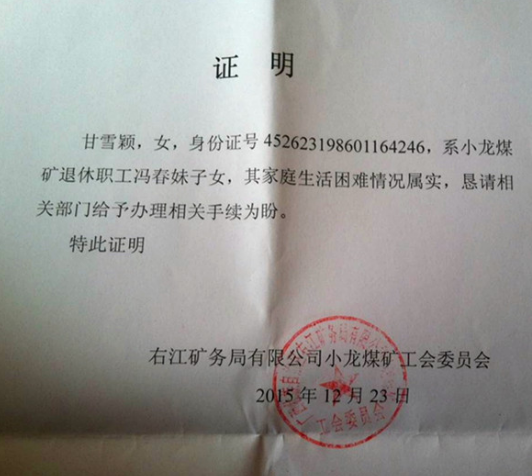范文一:轻轻地来与轻轻地走
轻轻地来与轻轻地走
作者:史铁生
来源:《语文世界(初中版)》2014年第12期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扑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范文二: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2013年09月10日 11:34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郭丽萍
作家史铁生生前多次表达,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
2012年5月5日是崔静宜95岁生日,护士特地讲病房用气球、彩灯、鲜花精心布置了一番。家里人还特地做了件喜庆的衣服,换下他平日长传的单调的病服
凌锋已与丈夫有过很充分的详谈,他们都选择真到了临终的时候,不去做无谓的“延长”,也要尊严死
原标题: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句脱胎于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化的语言,是史铁生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和他的主治医生凌锋等人的生死观。
记者_郭丽萍 北京报道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办公室里,凌锋在白纸上画了一条黑线,利落得像她多年的短发和身上的白大褂。在黑线的末端,她添了一个句号。
黑线是生命,句号代表死亡。对于做了四十年临床医生的凌锋来说,死亡确实就像文章里的句号一样平常,只是采用何种方式的问题。
“'尊严死’(DeathwithDignity)与'安乐死’(Euthanasia)不一样,”凌锋用笔尖指在黑线中间的某一点上说,“'安乐死’是生命还没到句号这个地方,按照病人的要求,为病人提前结束生命。”
笔尖移到黑线末端。“生命到了末期,尊重病人的意愿,放弃治疗,实现自然地死亡,叫'尊严死’,不违法。”
这些年,凌锋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实践者。她曾帮助著名作家史铁生和她的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而她自己与丈夫也已达成共识,他们都选择临终的时候,自然、有尊严地离去,不做无意义的延缓,把这个句号拖成省略号。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句脱胎于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化的语言,是史铁生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和凌锋等人的生死观。
1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2010年12月30日,凌锋接到了一个焦急的电话: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你去看看,帮忙抢救一下吧。
凌锋赶到的时候,史铁生已经躺在朝阳医院急诊区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微弱,瞳孔已经渐渐放大。经验丰富的她将预后(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告知了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
陈希米选择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措施,希望史铁生能平静地离去。她告诉凌锋,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只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史铁生多次表达,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凌锋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关于生命的体验、死亡的思考,贯穿了史铁生30多年的写作生涯。作为史铁生的主治医生和十多年的老朋友,凌锋读过很多他的作品,知道他怎么看待生死。他的生死观,早已概括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这篇文章里。
现在,死神已然站了起来,不由分说地。凌锋知道史铁生不想拖延,因此,她对陈希米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凌风环顾四周,急诊区里,挤挤挨挨排了几十张病床,躺满了人,打针送药,进进出出,闹哄哄的。凌锋当即把史铁生转到她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安排他住进较为安静和温馨的重症监护室单间。
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又在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郑重地签上名字。护士小心翼翼地为史铁生做着基础护理。
在亲朋好友以及天津医护人员的车队护送下,史铁生被转至北京武警医院进行器官摘取手术。史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但他一直硬撑着,以便让每一个要捐献的器官都处于最佳的移植状态。
2010年12月31日3时,到了武警医院后,史铁生才慢慢停止呼吸,表情安详得像睡着了一般。所有医护人走向他,在《安魂曲》中三鞠躬。
手术完毕之后,医生们为他做了最细致、完整的缝合手术。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机体中延续着生命。
凌锋亲手帮史铁生整理衣领,帮助家属收拾遗物、抬遗体。“他活着有尊严,死了也有尊严。”凌锋说。
2
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
—《康复文本断想》
凌锋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也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专家委员会委员。早在史铁生去世前那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就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有关倡导“尊严死”的议案。
在四十年的临床工作中,凌锋没少碰到各种例子。最极端的是,有一位病人早已经脑死亡,但呼吸、心跳、血压还用设备维持着。“当一个人不能自主地支配自己所有的一切,浑身被插满管子,又像翻麻袋一样的,由护士天天翻来翻去,你觉得他有尊严吗?”
人总是要死的,不应违背这种自然规律,或违背人本身的意愿。虽然现在的医疗已经发展到可以依靠设备来延长死亡,但在凌锋看来,这是一个浪费、尴尬而且毫无尊严的过程。
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具体怎样才是有尊严的死,对于最后死的状态、方式和过程,1000个人也有1000种想法。凌锋总结了自己的心得:“'尊严死’的本质是,生命句号来临的时候,病人的意愿得到尊重、满足。”
在史铁生去世两年之后,凌锋也帮助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这个轨迹与史铁生竟是如此的相似。在送走公公的过程中,无论是从医生,还是家属的角度,凌锋心里都觉得很欣慰,没有丝毫纠结。因为她觉得,她遵从了老爷子那些简单并且高尚的意愿,尽了全力让他走得安详、有尊严。
在凌锋眼里,公公一生波澜壮阔,一直是一个热爱生活,又很能够善待生活的人。
公公叫崔静宜,是个老革命。1917年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因为家境殷实,他上了高中。他的姐姐崔静吾是天津女子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参加了抗日,是个卫生员。1938年,公公也跟着入了伍,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在89岁的时候,公公发现血尿,检查后才知道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同时,他的右肺也发现了一块阴影,是个小小的肿瘤。由于创伤会比较大,还有风险,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所以只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和一小部分膀胱切除,也没做副作用大的放疗、化疗。
凌锋说,老爷子一直很乐观,他说要跟肿瘤争时间、争速度,而且还要战胜它。
经历过多年战争、“**”、曾痛失至亲、至爱,公公对生死早已看开。抗日战争期间,他的姐姐在带着30多个伤员转移的过程中,为了引开围剿的日本兵,被敌人的刺刀挑死。1949年后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公公,在“**”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他从打压、戴高帽、住牛棚、游街、批斗这些令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的遭遇中,都熬了过来,因为有婆婆的支持。婆婆张淑敏也是一位老革命,但在1974年因病早逝,让公公又一次面对了死亡。
“所以公公认为每一天都是赚的。”凌锋说,“当一个人对生死都很豁达的话,那他平时的待人处世就很不一样了,不会那么尔虞我诈、斗得你死我活。活着的时候享受每一天,也能坦然面对死亡。”
老爷子生活非常规律,一分一秒都非常准确,不管多累、多忙,每天的锻炼都不落下。即使是做完手术,也还按凌锋的要求,每天走1000步,所以恢复得不错。出院后,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走三四公里。虽年届九旬,他的脑子、耳音都很好。
3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我与地坛》
直到2011年,老爷子肺里的肿瘤发展到了拳头大,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活检结果是肺腺癌。凌锋一家人都认为,最好不要去动它,否则遭受的打击和痛苦更大。
从当年10月入院到12月30日转院,这三个月是公公最痛苦的日子。他一直喘不过气,在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就是没法躺平身子,屁股都快坐烂了,血液回流不上去,腿肿得严重。老爷子70年的烟龄,一直到85岁才戒,在呼吸困难的折磨中,痛悔抽烟太多,见谁都劝戒烟。
难受极了的时候,公公对凌锋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让我过去算了,太痛苦了,我这辈子知足得很。”
凌锋回答:“我前脚给你打针,后脚就进监狱了。你不能让我做一个谋杀者吧。”这种“打一针”过去叫“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广泛的争议,在中国,尚没有法律依据。
公公笑了。
不过,即使现行法律允许“安乐死”,凌锋觉得自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她很明白,这只是公公太难受时说的气话,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其实老爷子的求生欲望非常强。即使是在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坚持出去遛弯,扶着轮椅像小孩学步一样走路锻炼。凌锋也知道,其实公公还有三个愿望:第一是能过元旦,第二个是能过春节,如果能再好的话,最好能撑到5月过95大寿。他只是希望痛苦能够得到解决。
因此凌锋想了一切办法来减轻公公的痛苦,24小时吸氧,并且最大量,但没能有根本改善。她告诉公公,唯一的办法是切开气管,用呼吸机带动呼吸,但是这样就说不了话,不过可以用写字来表达。
4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史铁生,《病隙碎笔》
2002年,凤凰卫视主播刘海若在英国旅游的途中,发生火车出轨事故。经英国医院抢救后,刘海若被判定脑干死亡。她的家人反对这个意见,要求中国专家一同会诊。凌锋接到指令,飞往伦敦会诊。凌锋发现,虽然刘海若伤势严重,但仍是自主呼吸,因此她判定不是脑死亡。经过精心医治,刘海若逐渐恢复了健康。
“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这是美国医生特鲁多(E.L.Trudeau)的墓志铭。他不仅是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人,并创办了一所“结核病大学”,还在生前创建了第一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
对于这句铭言,有人说它总括了医学之功,说明了医学做过什么、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也有人说,它告诉人们,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治愈,更多的是帮助、安慰;还有人说,它昭示了未来医学的社会作用。
凌锋很推崇这句话。她认为,救死扶伤一直被认为是医生的天职,但其实安慰和帮助占了绝大部分。“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但不希望死变得那么痛苦、恐惧,有些疾病无法彻底治愈,因此怎样减少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一个重要命题。”
2012年元旦前夕,凌锋帮公公转到了两年前她安置过史铁生的宣武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并用上了一系列减轻他痛苦的措施。
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之后,公公终于可以躺平身子,腿上的浮肿不久就退了。凌锋给老爷子用了一种短效的麻醉剂,只要不舒服,就打开麻醉剂开关。虽然现在有很多可以减少病人痛苦的药物,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无法推而广之。首先是价格昂贵,不是所有人能承担得起,其次像这种麻醉剂得在严格的医疗条件下才能提供,因为它对呼吸有抑制,必须配有呼吸机。
呼吸顺畅之后,老爷子能在病床上看电视、写字表达了。借助麻醉药,一宿能睡得安稳,早晨药一停,他就醒了。如果要吸痰、大便,老人家痛得难受,就又把麻醉药打开。休息好了,就不会太难受,胃口照样很好。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海峡两岸的动态,最爱看的节目是《海峡两岸》。那会儿凌锋参加全国“两会”,还经常到医院跟公公聊一聊“两会”的情况。
老爷子爱笑,一直到临终也都是红光满面。医护人员也都很喜欢这位可爱的老头儿。
5月5日是公公的95岁生日。护士特地将病房用气球、彩灯、鲜花精心布置了一番。家里的一些成员也特地从国外回来跟老爷子团聚。一家人在病床边跟他合影,虽然他气管里接着管子,但脸上还是笑呵呵的。他们还特地做了件喜庆的衣服,换下他平日常穿的单调的病服。
在照顾老爷子的过程中,凌锋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向更多的病人实施这种无痛苦的临终关怀。凌锋说,很多的癌症的晚期都是痛死的。**1974年6月间因癌症晚期住院治疗,一年之后,他被癌细胞吞噬得只剩皮包骨,体重只有61斤。**在晚年一度支持安乐死。
5
呵,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蓝/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
呵,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这囚笼烧净/让我从火中飞入/烟缕、尘埃和无形/最后的归宿/是无果之行
呵,节日已经来临/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我已跳出喧嚣/谣言、谜语和幻影/最后的祈祷/是爱的重逢
—史铁生,《节日》
过完95岁大寿之后,老爷子不断地伸出三个手指,每次吃饭也只吃三口。保姆一直猜不着是什么意思,就找来凌锋。
家人都知道,凌锋对老爷子的心思猜得最准。他在病房里用来表达的字写得很潦草,但凌锋都能看出是什么字。
凌锋一到病房,公公又伸出三个手指头。她俯身问:“爸,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想走了是吗?”
老爷子点了点头,没再伸手指。
再往后,公公的意识一天天地丧失,最后肾衰、无尿。医生们建议用透析,但体内的水排不出来,整个人会浮肿变形。
凌锋觉得没有意义了,因此决定不做透析,让老爷子自然地走。她很清楚,老爷子肯定不愿意以这种状态离开人世。“他是那么爱整洁、那么帅的一个老头儿,最后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他能愿意吗?肯定不能。”而且他已经陷入昏迷,叫不醒了。
89岁那年入院做手术的时候,公公就已跟家人要求,他们必须告诉他所有的疾病,而且必须讲得特别透。他还说过,不要无谓的检查,他不愿意很痛苦地活着,并把医疗决定权交给凌锋。
家人的意见也都很一致。“我们家很开明,对这个问题都有共识。”凌锋说,“公公清醒的时候很享受他所有的一切,当他不能享受的时候,不想再这么拖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顺。”
2012年5月23日,凌锋做出了与当初陈希米同样的选择,放弃治疗。家人都在身边,老爷子走得无牵无挂,神态非常安详。
进协和医院的时候,公公就知道住进去是出不来了。他仔细地跟家人商量了身后事:不要举行追悼会,通知亲属举行遗体告别就行了。他还交代要树葬。
凌锋还帮公公实现他的遗愿,死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器官留下。虽然80岁以上的任何器官都不能用了,器官没捐献成,但他做了全身的解剖。病理解剖报告还是为医学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信息。
凌锋一家人只在家庭内部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放了一个回顾老爷子生平的PPT,配了点音乐。除了家人,只请了公公病房的医生、护士。在最后的5个月里,医护人员都跟这个慈祥的老爷子成了好朋友。
遵照老爷子生前的意愿,凌锋直接把他的骨灰和先前早逝的婆婆的骨灰,合埋在树下,没用骨灰盒,这样才能如他生前所说,被树吸收。原本家人已经在屋前种好了一棵菩提树,因为老爷子觉得前面太闹腾,所以他们在后院重新种了一棵银杏。他们还曾把种好的树拍了照片,带到医院给老爷子过目。
在树下,家人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墓碑。墓碑上的文字,老爷子生前就有交待。老爷子喜欢花草,所以银杏树下,总有点点的小草花,橙的、黄的、白的三色。石牌就掩在花丛里,他们回家的时候,时不时要去看看,把墓碑擦一擦。
凌锋说:“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思念,但是没有悲伤。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尽心尽孝,在他身后对他所有的意愿给予满足,身后仍然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欣慰的事情。”
她还替老爷子在墓碑上面刻了一句墓志铭:“我们悄悄地来,也悄悄地走,留下一片绿,庇荫后人。”
这是凌锋对生死的理解,也是对两位老人一生的诠释。她已与丈夫有过很充分的详谈,他们都选择真到了临终的时候,不去做无谓的延长,也要“尊严死”。
范文三: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维普讯资http://w ww.cqvipc.m
: o_雹 :衷齐
经心地 和 附, 悯我都已经 得 不那么活在意 死了 。
这就是 说
正.在 轻轻地走 ,我 灵 魂 在 离开 这正个 残损不 堪的 壳躯 ,步步告别 一 着 这 世个 。界 这 样时候的, 不知 别 人会怎样 , 则想其尤想起轻轻地 来神的 秘。我 如 比 想起清晨 晌午和、 晚变幻 傍的 光 阳 ,一起 方蓝 天,想 个 一安 的小静院 ,团 面扑 而 来一的 柔和的风 . 风中仿从佛 就有来 母亲和奶 轻奶 的呼唤声… …不知 别 人是否道 也会 像一我样 , 由地衷讶 惊 日呢:?往日 的切一都 到哪 儿了? 去往
生命 的 开最 是玄端妙,完 的全 中生有 。好无 没 儿的影忽 你就然进 入 了种情一 .况 种一 况 引情 另一 种出 况 情, 理 成顺章 衣天 缝 , 一无来二 便连 去 出接个一现 世实
界
。 很的像电 ,影无 的幕 银上 真,虚 比如说 然 忽有就 一了 个在 草丛里玩蹲耍的 子 孩 , 太 阳 耀照 , 他照耀 远 着山、 树 近和丛草 中的一条 路 小 然后孩子 玩腻。 了, 沿 小路 蹒
跚往地回 走 于. 又是 引 出 小尽路 头 的 座一子房 ,门前正在张 望 他母 亲 的 ,头埋 于烟斗 或报 纸的 父 亲 ,出一 家 个 引 随后 ,出引个一 世 界 子。只是 跟随 这一系列情 况 走, 有
孩
维资讯普htt p:/ww/w.cvqpico.
m
些一闪即 , 有些便逝 成 不为更改可的历史 , 及不 以可更改的 史 的原历因。 这样, 于
有 一天终 孩会子想起 开 端 的 妙玄 :缘无 故 无 .正如先哲 所 —言— 人是 被抛 这 到个 世 界
新
、
…
一
一
…
。
…
…铋
…
、
它 看。 里 有些 屋暗昏, 窗外 光阳明 媚。 近 是一排绿 油处 的榆油矮树 ,墙越过 树矮榆 远墙处有两 棵大枣 ,树枣树 黑 枯枝 的镶条 进蓝嵌 天, 下是 树周四静 的静廊窗。— — 枣 与 界 世最 初的相就 是见这 , 简样 , 单象印 刻深。复杂 的 界 世在尚远 , 但 或者方, 就它 在那安恬 蹲时 的四间窃笑周 ,看 一幼稚 个生的命慢慢睁开 眼睛, 萌 生 欲着 。望 我蹒 跚地 出走屋 , 门进院 子 个真实 的世 ,才界 开始提 凭证 。太供阳 晒 的热 走 一花 草的气 味 阳晒,热砖石 的气 味的 太 阳,在光风 舞蹈 、中流动 。青砖铺 成 的 十字 甬道
连接 起四面 的 屋 , 院房 隔成 子四 均块等的土 地 , 把两块 上 面各 有 一棵枣 树 ,两块 另
种满 了西 莲蕃 。西 蕃顾 莲开自着 大 硕花的 朵, 蜂 蜜在层 叠花瓣 中间的钻进钻 , 嗡 地嗡采开 蝴 。蝶 闲飘 逸悠 ,飞去来, 飞 悄声 息仿无幻佛影 。枣
树 落下移动 满树影的 , 落满细 碎的 枣 花。青 黄的 花枣 一层像粉, 覆 盖着 地上的青 苔, 滑 ,很 上踩 要去小 心。 天 上. 者是 云或彩里, 有 些音声, 些 有缥不缈 所知在 声 音—的 风声 —?声 ?铃是还 歌 声? 说不 , 清久很我 都知道 那到不底 是 什么音 声 ,我 但走 一那块蓝 天到 面下就 听见 了他 ,甚在襁 褓至中 就已 听经 他了 见那 。音声 朗 , 欢欣 清, 悠扬 扬不 悠紧不慢 , 仿佛 是生 命有的 召固 , 执意 唤你去要注意 他, 寻找 他、 去 看望 , 他甚 或去投他 。 奔
我迈 过高高的 门 ,槛难 走地 出 门院, 艰 眼是 前一条静安 的小 街 细, 长 整、 三, 规 两 个 陌生 的影走过身 向东,边的 朝 阳 走,走进 西 边的落 。东日 边和边 都不西知 向通哪
里, 不都 知连着接 么 , 什唯那 妙美的 声不惊 音懈不, 如如风流 … … 真是奇神。很 可能 , 生死都和不 取过决于 察观, 取 决观于 察的远与近。比 如 当,
一
;
二
f
颗
离 我们数 十万 光年距的 星星实际 已早灭熄,它 正却在 我 的视们 里度着 它 野的
青 时年光 。时间 制限 我们了, 惯 习制 限了们我, 言般 的论舆 让 我们 于陷 实际, 我们 在 谣 让
白 的魔昼法 中闭 目塞听 敢 不为妄 。白是昼 种一 魔 法, 一符 咒种, 死 僵的则规 行 让 畅无 阻 实.际消 掉磨神 奇所有。的 人都 在昼白的 魔法之下扮演 着 张 、紧 让呆板 角色 , 的
一
切言谈举止一切 思与绪 梦想 ,都 佛被仿 设 的预程 所序定 。
我 的圈躯体早 被 已固定在床上 , 定 固在轮椅 中 , 我心 魂的 常黑 夜在 出 行 离, 但 脱
o
维资普 ht讯p://wtw.wqciv.cop
m开 残的躯 废壳, 脱离 昼 的白 法 魔 ,离 际实 , 脱在尘 稍嚣 的息夜 的界世里 游 逛,听所 有 的梦者 说 ,诉 看所有 放弃了 尘 角色世的游魂在 夜 的空天 和旷 中揭开 另一野种戏剧 。 风 ,处游 走 四, 串联 夜起 消息 的,沉 睡的窗口 沉到 睡窗 口,的 从 去望探 白被 忽略 了 昼的情。另一种 心世 界 蓬,蓬 勃 勃 的声,音无比辽 阔 。是呀 。 夜那才 是写 作 啊至。于文 学 我说,过 我跟它好像 大不边沾儿 , 我一 向心 往 只的 这是自由 夜的行. 到 切一心 去
魂 的由 衷 所 在的
回 读
史铁生 的篇这《轻 轻走地 轻轻与地来》 仿佛 是在就读 史 铁 的生魂 灵,他的 文字没 那种 有张 扬的 坚强不屈“ ” 气 的
息
,多 的一是种对生命体验娓的道娓 来。铁 史就是 生以明更 净而 睿 的文智, 那样字 粹地
纯
表达 自着的灵魂己 , 察省 着 自的 内心己, 他谈生 命、 生活、 童 年、病 、 情 谈 谈谈 死谈 亡 ,奈 无见中著执, 阴 中郁见微 笑 苦,难 中见望希, 平淡见中刻。深他 对亡死的份坦那 , 对苦然的那份微 笑难 对命运竹,份那厚 宽 , 足以让人敬 。史仰 生的写铁与作他的命 生全完同 在构 了 一起 他,残缺 用的身 体 ,出最为健全了 丰满 的而想思, 说种勇这 气和执 ,深著深唤起 地了我对们 身自 所处境遇的警醒 和关 怀史。铁生 验到体是生命 的苦难的. 达表出的 是却 明和欢朗
乐. 他睿的言智辞, 能 够照 亮们我日益 暗的幽内 和心脆 的 弱
心 灵
命运。将史 铁 生限定在 轮椅上了,剥夺 了他 外部生的 .活
他 就用思 想做 脚 , 心内走 去 , 往 越 行 越远 渐 , 入 进 种一冥 渐 的思 生活史铁。生 断 追不 新 寻的超 越,其 他 家相 作 .比 更 至 与甚
高
度程地 把生活握在掌自 手 己。谦和 、中实而 顽的强轮椅 平家用笔作在灵魂 的深邃 之处领引们,我他 站在 是生了命 的至
高点上, 居种 高临 下俯的瞰 , 那 那种 宽 广 与 博大 乎, 可以 将 几
生命 中一切的囊括 与覆 。盖这从个义意说上 史铁,生残缺 的 生命到达了极 与巅致 峰 射着最璀璨放光的。华
海(涛) 韩
范文四: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史铁生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逝去的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选自《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有删节) 14、从文意看,作者说“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玄妙”在哪里,(6分) 答:
15、作者笔下的一个普通四合院窗外的景物有什么特点,文章为什么要写到这些景物,(6分)
答:
16、仔细阅读最后一段文字,作者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在“夜的世界里游逛”的目的是什么,这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创作观,(4分)
答:
17、这篇文章的标题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标题好在哪里,(6分)
范文五: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轻轻的走与轻轻的来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的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的。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说过,徐志摩这首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来,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次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先是这,再是那,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的很平静,我漫不经心的附和,我们都已活的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的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的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铺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的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去了?
生命的开端是最玄妙的,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的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
的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的它的母亲,埋头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然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状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研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片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颗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的,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学,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踏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的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
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一经流露出欣慰,看我渐渐长的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的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匀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之中钻进钻出,。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飘渺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片蓝天下面就听到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到了他。那声音晴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是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的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西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道通向哪里,都不知道连接着什么,惟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圈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
稳的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的近了,飞过头顶,又紧紧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已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街上,痴迷的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人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会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是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那些欠真实的舆论让我们限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长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幽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我和它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