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一:囚犯困境是什么?
管理资料下载 http://www.downhot.com 最好的管理资料下载网站
囚犯困境是什么,
囚犯困境 囚犯困境是指这样一种情形,此时两个人(或厂商)合作要比不合作好,但是每个人都觉得不合作符合他的利益,因此每个人的状况都要坏于如果他们合作时的境况。 概述 囚犯困境(Prison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不会一样。 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为。这时,合作可能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欺骗的动机这时可能被受到惩罚的威胁所克服,从而可能导向一个较好的、合作的结果。作为反复接近无限的数量,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 囚犯困境的主旨为,囚犯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犯招供,因为囚犯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之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经典的囚徒困境 1950年,由就职於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
塔克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後来由顾问艾伯特?(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於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PPT模板下载 http://ppt.downhot.com/ 最好的PPT模板下载网站
管理资料下载 http://www.downhot.com 最好的管理资料下载网站 [扩展阅读]
魔方教程 http://www.downhot.com/guanli/42969999.html 微信电脑版 http://www.downhot.com/guanli/44564173.html 身份证号码和真实姓名 http://www.downhot.com/guanli/44861147.html excel表格的基本操作 http://www.downhot.com/guanli/42376279.html 八一建军节 http://www.downhot.com/zt/81/
辞职报告 http://www.downhot.com/zt/cizhibaogao/
大写数字一到十 http://www.downhot.com/guanli/44564271.html
[推荐网站]
PPT模板下载 http://ppt.downhot.com/
PPT模板下载 http://ppt.downhot.com/ 最好的PPT模板下载网站
范文二:困境儿童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新困境儿童?
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决定,针对困境儿童面临的突出困难和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建立健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综观《意见》的内容,有三大亮点值得关注:明确界定困境儿童定义;加强困境儿童保障,网络+阵地+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新困境儿童”是指:很多表面上几乎看不出问题,大多数生活环境相对优越,经济条件好,父母受教育程度高,重视教育,他们成绩好,甚至优异。然而,他们长期身心承受的痛苦压力和巨大成长风险往往不被家长、老师觉察和了解,无法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力支持,最后部分孩子走向绝路,如自杀、自残等。这样家庭的孩子往往由于
1
家长老师缺乏关注和警惕,被称为隐性困境儿童,相比而言,他们的风险由于不被重视反而更加危险。
附件列表:
2
范文三:“空巢老人”的困境是道德的困境
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四德”建设提到事关和谐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 2010年6月27日,爱心敬老院,76岁的李素琴老人以不赡养老人为由把儿子告上了法庭。敬老院的工作人员称李素琴老人的儿子自从把她“寄放”在敬老院之后,就再也没来看望过老人。每次打电话来联系都说工作忙,明天就来。可是明日复明日,这一下子就过了半年之久。李素琴老人也变得越来越忧郁了。无奈之下,她决定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经过法院工作人员的调解,最终李素琴老人的儿子接回了自己的母亲,并保证以后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一定照顾好母亲,尽好孝道。 目前,老人们需要很多的关心和爱护,需要用立法等手段来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伴随着新老年法草案的推出,尤其是草案中将子女应“常回家看看”的内容写入条文,并增加了“精神慰藉”等,热议声此起彼伏。 去年,某区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李延安老伴去世后,儿子工作繁忙,几乎很少来看望老人。在一次社区组织的太极拳比赛中,李延安认识了王淑玉,得知王淑玉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丈夫经常酗酒后对其和孩子进行殴打。于是,李延安经常开导王淑玉。两人十分投缘,经常一起聊天。 可是,没过多久,李延安患上了癌症。王淑玉很难过,自愿提出照顾李延安。李延安的儿子觉得王淑玉和父亲原本就是朋友,而且很投脾气,非常适合照顾病重的父亲,就雇佣了王淑玉。 王淑玉搬到了李延安家里,承担起了保姆的责任,虽然是保姆,但王淑玉却像亲人一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位病重的老人。 不久,李延安去世了。王淑玉在其枕头下发现了份报恩遗嘱:“感念王淑玉对我好,在我患病期间周全照顾,她是个好人,也是个可怜的人,为感谢她,我自愿将我的一套住房和房内的财产全部赠给她,任何人不能干涉。” 王淑玉的丈夫和儿子知道此事之后,都不能原谅她,把她赶出了家门。李延安的儿子得知后,十分气愤,“王淑玉不过是我雇请的保姆,充其量也不过陪我爸过了一年多,凭这些就可以要房子?” 无家可归的王淑玉没有办法,欲求助于法律讨回公道。 遗产赠保姆,法律可以支持,遗产赠第三者,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王淑玉在这份报恩遗嘱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保姆,还是第三者?介于两者之间的她,又如何在法律上寻找到平衡点呢?李延安老人的遗嘱又是否有效呢? 由“空巢”家庭老年人引发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 “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由于目前社会“空巢老人”增多,“常回家看看”被列入了“老年法草案”。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更加注重了老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也是老年法草案最突出的亮点。 律师点评 魏位 山东岛城律师事务所 当今社会“空巢老人”的现象愈加凸显,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上述案中李延安老人生前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给王淑玉的行为是否有效呢?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根据该条法律规定,王淑玉对李延安生前悉心照顾,李延安怀着对王淑玉报恩的心立下了该份遗嘱,自愿处分其个人财产赠给照顾自己的王淑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人不得干涉,包括李延安的子女,故王淑玉要求受赠财产请求诉诸法律会得到支持。通过这则案例也折射出当今社会,“空巢老人”这样一个群体,如今面对更多的是无奈,我们在赞扬王淑玉照顾老人的同时,是否也该问一下作为“空巢老人”的子女,我们又做到了些什么? 本刊视点 “常回家看看”,本是人之常情,更是儿女对父母的基本义务,但对大量“空巢老人”而言,却变得越来越奢侈,于是一曲《常回家看看》唱红了大江南北。说实话,这支歌旋律一般,歌词很婆婆妈妈,但却一炮走红,其神奇的魔力何在?显然,缺少亲情和温暖的老人太多,在空巢中四顾无侣的老人太多,这是一种共同的疼痛,于是一首寻常的歌,似乎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空巢老人”的困境,是道德的困境,更是文化的困境。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生尚不足百年,“百年树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指的是一个文化建设周期。文化生态一如自然生态,一种良性循环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过程,所谓五代才能培养贵族,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要想弄清楚我们当下的道德文化困境,有必要梳理一下百年来的历史风云。 传统的父子关系,最形象的范本是《红楼梦》,贾宝玉跟贾政的关系,形同鼠猫,即使贾政心情不错对儿子很满意时,也动辄就是一声“畜牲”的断喝。更极端的例子则是“郭巨埋儿”:面对饥馑又要恪守孝道,郭巨的解决之道是“埋儿”。显而易见,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尊老”与“爱幼”火拼,结果郭巨做了坚定的父母党。不过,这种看似轻松的道德选择,其实已经埋下了更深的哲学悖论:如果埋了儿子,还有未来吗?因此,对以忠孝为基础的传统伦理,曾有学者概括为“杀子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觉醒与启蒙,本质上是对“杀子”的清算与反扑,对此,《家》是不错的注脚,年轻人追求个性自由与离家出走,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诉求。不过,相对于更迫切更棘手的民族独立与革命,涓生与子君的矛盾纠结,显得太小资太轻飘甚至是无病呻吟。这是个血与火的时代,斗争始终是最高亢的主旋律,所以传统伦理很快就代之以革命伦理,到**时期学生斗老师,或者儿女宣布脱离家庭关系,便不仅是反传统伦理,甚至已经反生物学。 根本的游戏规则受制于文化哲学。我们面对的是文化的重建。几年前,曾经有一位父亲要去少林寺习武,因为他在儿子的拳打脚踢之下已经度日如年,他想学一身武功好制服那个忤逆不孝的儿子。这种啃老虐老的语境,是极具讽刺意味的,那个古老的“杀子”,这会儿就回到了“杀父”,转了一圈,只是完成了一次“换岗”。 这对父子,演绎的已经是赤裸裸的丛林故事,即谁拳头硬谁就是大爷。明乎此,是道德或法律建设的前提,也就是说,呼唤一种启蒙意义上的大爱,追求一种更平等的人格,缔结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建设一种呵护弱者抑制强者的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起点。(乌耕)
范文四:道德困境之困境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11, 1702–1712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1702
道德困境之困境 —— 情与理的辩争
喻 丰1 彭凯平1,2 韩婷婷3 柴方圆1 柏 阳1,2
(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 USA)
(3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道德判断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评价性活动之一, 但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争执不休。从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论争到发展心理学家对道德推理的关注, 直至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对情绪的重新审视, 道德判断的决策机制已经演变为多种模型相互竞争的局面。在回顾和分析道德判断各种理论的基础上, 阐述了情绪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关注道德推理的实际作用, 并当运用更为先进的操纵手段, 同时注重情境的影响来考察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问题。 关键词 道德; 道德判断; 道德推理; 情绪; 双加工理论 分类号
B849:C91
情形一:一辆列车疾驰而过, 前面的铁轨上绑着5个人, 如果任由列车行驶, 那5个人必将罹难, 不过你站在铁轨旁边可以选择扳道来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但是那条岔道上也绑着1个人, 扳道的结果是这个人必定遇难。请问这时你是扳还是不扳?
情形二:一辆列车疾驰而过, 前面的铁轨上绑着5个人, 如果任由列车行驶, 那5个人必将罹难, 你站在铁轨正上方的天桥上, 你的前面有一个胖子, 你可以将他推下天桥以阻挡住列车的运行来营救那5个人, 不过这个胖子会遇难。请问这时你是推还是不推?
同样是杀死1个人来救5个人, 在前一种情形下, 大多数人选择了扳道, 而在后一种情形下, 大多数人选择了不推(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 & Cohen, 2001)。这个列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哲学家们并不陌生, 他们忧心忡忡地试图了解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Foot, 1967; Thomson, 1976)。但其实应该怎么做并不复杂, 伦理学家们也有着自己的信条, 秉持义务论(Deontology)的哲学家们认为虽然能救5个人的命, 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杀死那1个本不该死的人; 而秉持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的哲学家们
1702
1 所谓情与理
社会生活中, 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是人类习以为常的活动。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忠与奸、正与邪、是与非、对与错都是我们对人、对己、对事、对物所贴的标签。我们会说一个人的道德(morality)是高尚的, 也会说做某件事情是卑鄙的。道德似乎是在教我们应该如何行为, 这也是传统伦理学(Ethics)所谓之观点。伦理学家们认为道德讨论的是“应该” (ought), 而科学研究的是“是” (is), 两者必然是渐行渐远、永无交集; 但当代心理学家们却认为这二者终将汇入一流、殊途同归(Greene, 2003)。因此, 面对同样的道德困境(moral dilemma), 哲学家们会在躺椅上思考着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一困境, 心理学家们会在实验室中观察人们到底是怎样解决的, 为什么人们又会这样去解决。总有一些情形让我们跋前踕后、进退维谷, 使我们在殚精竭虑、黯然神伤之后仍然举棋不定、踌躇不前。很遗憾, 这样的选择我们经常会碰到, 比如以下两种情形:
收稿日期:2011-03-21
通讯作者:彭凯平, E-mail: pengkp@mail.tsinghua.edu.cn
第11期 喻 丰等: 道德困境之困境 1703
则坚持, 在行为后果上杀1个人能救5个人, 这样的事情就应该做。显然, 结果论只关注行为的后果(consequences), 而义务论则关注行为的过程, 强调责任(duties)。让哲学家们疑惑的是, 无论你秉持哪种观点, 在两种情形下每个人的选择应该是一致的, 但实际情况为何大相径庭?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哲学家,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此时心理学家们的科学思想和实验方法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 心理学家们开始关心这个不一致的事实, 但只是想去了解事实究竟是什么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心理学家们开始对这些道德困境进行实验研究, 研究卓有成效, 不过与此同时, 他们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那便是情与理的争执。情与理, 是世俗所谓的感情(sensibility)与理智(sense); 是伦理学所谓的情感(passion)与理性(reason); 是心理学所谓的情绪(affect)与认知(cognition); 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道德心理学所谓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与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2 情与理的历史交织
影响道德判断的究竟是情绪还是认知?作为有着很长过去但只有短暂历史的心理学来说, 我们仍然要把这个问题抛向历史久远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 以求寻根溯源。每当某一学科就某一问题向上追溯之时, 似乎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那些先哲们, 然后罗列出一长串思考过此问题并提出过见解的思想家们。但这里我们仅仅探讨两位在情与理的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代表人物:休谟(David Hume)和康德(Immanuel Kant)。休谟道德观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 道德是自然的(naturalistic), 即认为道德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 第二, 道德研究是经验的(empirical), 即理解道德应从研究人类着手, 运用实证方法来进行; 第三, 道德判断是基于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的, 即情感驱动了道德判断; 第四, 在道德判断中, 理性可以起作用, 但不能单独起作用, 它必须依附于情感; 第五, 道德与宗教并非一码事, 道德是情感指引的, 而非上帝指引的; 第六, 休谟的思想偏向结果论、导向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但其中也包含美德伦理学, 即那些能使我们美好生活的特质(Cohon, 2010; Denis, 2009)。简言之, 休谟认为情感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 而理
性只是情感的奴隶(Hume, 1978, p. 420)。但康德并不同意这一观点, 他与休谟在很多观点上截然相反, 他认为:第一, 道德研究不应采取经验方法, 而应采取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去寻经问典; 第二, 道德是基于理性的; 第三, 驱动道德行为的不是情感而是责任(duty); 第四, 康德的伦理学思想是义务论的(Johnson, 2010; Denis, 2009)。简言之, 康德认为影响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是理性, 正是严密的推理使我们作出道德判断, 而情感在其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休谟与康德二人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影响着心理学对道德的研究, 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历史中, 康德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即认为道德判断中的理性最为重要。心理学中道德研究的拓荒者是发展心理学家, 而皮亚杰(Jean Piaget)是当仁不让的先驱人物。皮亚杰致力于解决根本的认识论问题, 而他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儿童对逻辑、数理和科学概念的推理来进行研究(Lapsley, 2006)。幸运的是, 当时皮亚杰的研究涉及到了道德领域。他的方法是给孩子们讲两个故事, 问孩子们哪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更糟糕: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个在帮助妈妈时无意中打碎了15个杯子的小朋友; 另一个是自己为了偷吃食物而碰碎了1个杯子的小朋友。皮亚杰发现, 10到11岁之间的孩子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并不相同, 小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更多认为打碎15个杯子的小朋友更坏, 而大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则不会都去责备那个无意打碎15个杯子的小朋友。皮亚杰把前一阶段叫做他律(heteronomy)阶段, 把后一阶段叫做自律(autonomy)阶段。他律阶段的孩子们做道德判断是依据一些规则来进行推理的, 这些规则由父母或者权威制定, 孩子们认为这些规则是固定的、绝对的、刻板的、神圣而不可更改的; 自律阶段的孩子做道德判断时仍然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来推理, 但是他们却不再刻板化地看待规则, 他们更加灵活, 可以认识到道德判断是相对的, 在大家都认可时, 道德的规则是可以改变的(Crain, 1985, pp. 118?136)。当然, 根据皮亚杰的研究, 按照他律阶段的刻板规则做出的道德判断一般是结果论的, 而根据自律阶段的灵活规则做出的判断则可能是义务论的。在皮亚杰的基础上, 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将这一研究传统推向了顶峰。科尔伯格坚持人类的道德发展必须根据他们如何推理来进
170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行判断, 是推理决定了做出何种道德判断。他也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某人的妻子身患重病, 濒临死亡, 只有唯一的药能解其绝症, 但发明此药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 此人凑不到足够的钱, 只能去偷药救妻。然后科尔伯格便询问研究参与者, 此人该不该偷药, 为什么?科尔伯格关心的不是“该不该”, 而是“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做道德判断时的推理。他根据人们不同的道德推理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道德(preconventional morality)、习俗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和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前习俗道德阶段的道德推理是基于他律的、自我兴趣的规则来进行; 习俗道德阶段的道德推理是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社会性规则来进行; 后习俗道德阶段的道德推理是基于社会契约和普遍道德原则等规则来进行(Crain, 1985, pp. 118?136; Lapsley, 2006)。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观如图1所示, 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建立于道德推理之上, 他们并不关心情绪在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只承认道德判断中认知的贡献。在科尔伯格之后, 发展心理学家们对道德的研究仍然还是承袭着道德判断的认知和推理观。
心理学中1950年代兴起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 (Miller, 2003)之后, 社会心理学家们也开始了对道德问题的探索。巴伦
图1 认知发展观的道德判断模型
(Jonathan Baron)首先借用了启发式(heuristics)的概念, 认为非结果论的道德判断更多是基于启发式的(Baron, 1994)。启发式是我们做决策时所依据的快速而简便的规则, 不过根据启发式来做决策时, 有可能造成决策的偏差(bias) (Tversky & Kahneman, 1974)。承袭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道德判断时的主要依据便是启发式, 而其主要过程便是认知。他们认为:第一, 做出道德判断的依据不是审慎的道德推理, 而是基于启发式的道德直觉, 所谓道德直觉就是启发式; 第二, 驱动道德行为的启发式和驱动其他行为的非道德启发式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道德启发式只是人类决策和判断中启发式在道德情境中的特例而已; 第三, 道德启发式是无意识、自动化地发生的; 第四, 根据启发式来做道德决策确有坏处, 容易造成决策偏差, 但也有益处, 它能帮助我们快速高效地处理问题,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依靠它所做出的决策是合适的; 第五, 做出道德决策时, 情绪没有起什么作用, 道德启发式是无意识的认知过程, 并没有什么情感过程参与其中(Sunstein, 2005; Gigerenzer, 2008; Sinnott-Armstrong, Young, & Cushman, 2010)。如图2所示, 实际上, 道德启发式的观点认为, 道德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确实不起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是道德直觉, 不过道德直觉也是认知过程, 并不包含情绪在内。
图2 启发式理论的道德判断模型
认知革命的几十年之后, 心理学中的情感革命(affective revolution)兴起(Fischer & Tangney, 1995)。人们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情绪, 休谟的观点重新得到了极大的复辟(Miller, 2008)。海特(Jonathan Haidt)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海特(2001)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SIM), 他同样承认做出道德判断时依赖的是道德直觉而不是道德推理, 但是海特认为虽然道德直觉和道德推理是两种认知过程,
但是道德直觉这一认知过程中含有大量的情感成分, 正是这些情感成分使我们做出道德判断(如图3所示)。具体来说, 海特认为:第一, 道德信念和道德动机来源于道德直觉, 而道德直觉是进化而来的; 第二, 道德判断是快速且自动化的道德直觉过程的产物, 而缓慢且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发生在道德判断之后; 第三, 在决定道德判断的直觉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绪而不是认知; 第四, 道德推理的作用在于事后解释, 当我们做出
第11期 喻 丰等: 道德困境之困境 1705
了道德判断后, 我们用道德推理来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理由; 第五, 虽然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能够发生, 但它很难改变由情绪所产生的道德判断结果; 第六, 若要改变某人的道德判断便需要改变其道德直觉过程而不是改变其道德推理过程, 因此说服等社会影响过程便是改变另一个人道德直觉的过程(Haidt, 2001, 2007, 2008; Haidt, & Bjorklund, 2008; Haidt, & Kesebir, 2010)。在海特看来, 情绪是做出道德判断的决定性因素, 推理过程根本不能和直觉过程相提并论, 认知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道德判断的结果寻找理由(Haidt, 2010)。这正应验了休谟的话:“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Hume, 1978, p. 420)。
海特对情感过程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批评, 而其中最为有力的批评来自格林(Joshua Greene)。格林承认情绪在道德判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他并不认为道德判断的做出仅仅只依赖情绪, 而道德推理这样的审慎认知过程也有其作用(Greene, 2007)。格林认为, 要认清情绪和认知的作用必须先区分道德判断的类型, 即结果论的道德判断与义务论的道德判断(Cushman,
图3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Young, & Greene, 2010)。做这两种判断时, 人类所依赖的是不同的加工过程:做出结果论或者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判断依赖于受控的认知加工过程, 而做出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则依赖于直觉性的情绪反应(Cushman et al., 2010)。格林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 (如图4所示)与海特的社会直觉模型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 双加工模型认可情绪的作用, 但它同时也强调基于规则的、受控认知过程, 特别是有意识地应用功利主义道德原则; 第二, 社会直觉模型认为社会影响只能通过改变某人的道德直觉而发生, 而双加工模型则认为社会影响也能通过直接作用于某人的道德推理而产生, 即对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与自己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承诺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有意识的评价(Paxton & Greene, 2010)。格林的双加工模型实际上是对休谟与康德关于情感与理性的观点的调和。
对比四种理论, 我们会发现, 它们在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对做出道德判断所起的作用上分歧很大, 而且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发生机制也并不一致。具体的对比见表1。
图4 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
表1 四种道德判断理论的对比
认知发展观
情绪过程 没有直接作用
认知过程 审慎、有意识; 对应道德推理
道德直觉 对做出道德判断没有
直接作用
道德推理 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启发式理论 没有直接作用
快速、无意识; 对应道德直觉
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对做出道德判断没有直接作用, 但可以为道德判断提供事后解释
社会直觉模型
快速、无意识; 对应道德直觉
审慎、有意识; 对应道德推理
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
对做出道德判断没有直接作用, 但可以为道德判断提供事后解释
双加工模型
快速、无意识; 对应道德直觉 审慎、有意识; 对应道德推理 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
的原因 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的
原因
170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3 情与理的重重疑问
3.1 道德判断中情绪的作用如何
从当代研究来看, 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海特的社会直觉模型甚至将情绪置于道德判断的中心位置。海特发现, 在对一些无礼的活动做道德判断时, 情绪反应比对伤害的评价更能预测道德判断的结果(Haidt, Koller, & Dias, 的哭闹之声会招来敌军使所有人丧命, 你认为哪种选择是合适的(Greene, Nystrom, Engell, Darley, & Cohen, 2004)? 结果发现, 不同的脑区激活能够预测人们的道德判断:与情绪有关的脑区激活, 可以预测人们的义务论道德判断, 即不捂死自己的孩子; 而与审慎认知加工有关的脑区的激活, 可以预测人们的结果论道德判断, 即捂死自己的孩子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安全(Greene et al., 2004)。
1993)。如用国旗擦洗厕所、吃掉自己养的但被车撞死的狗、不遵守亲人临终时的承诺、兄妹接吻、超市买回冻鸡先与之做爱而后食之等情境下, 人们说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这更多的是基于他们的情绪反应(Haidt et al., 1993)。甚至人们在听到这些故事时, 会很快地做出判断, 说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但当研究者们询问他们为何错误时, 大部分人会沉默良久但做不出任何解释, 只能说“我就是知道这是错误的” (Haidt et al., 1993; Haidt, 2001)。
不仅行为数据显示出情绪的作用, 生理学证据同样佐证了在道德判断中情绪扮演的重要角色。格林等人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的方法对回答列车问题的实验参与者进行扫描, 他发现造成大多数人会选择扳道来杀1人救5人, 而不愿意将1人推下天桥来救5人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两种情境下激活的脑区并不相同(Greene et al., 2001)。在选择扳道的情境下,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等与审慎的认知加工特别是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 而在天桥问题上,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与杏仁核(amygdala)等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会被激活(Greene et al., 2001; Haidt, 2010)。这似乎解释了哲学家们争议的问题, 为何同样是杀1人救5人, 人们的选择如此不同?心理学家可以回答说, 这可能是由于在天桥这种涉及自身的情境相对于扳道这种不涉及自身的情境下更多地受到了情绪的影响。之后, 研究者们用一个既可以做结果论又可以做义务论的情境来考察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 如:你正和众人藏身地下室躲避敌军的屠杀, 但你的孩子开始哭闹, 你必须捂着他的嘴来阻止其声音传播而不致被敌军发现, 但若长时间捂着他, 他会窒息而死, 若不捂着他, 他
这些研究实际上还是以道德判断来反推情绪的作用, 即我们观察做出道德判断甚至是不同形式的道德判断时的心理过程。而要证实情绪的作用, 直接的办法是操纵情绪来观察人们之后的道德判断, 这也是更为逻辑的方法。用催眠状态来操纵情绪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研究者们告诉催眠状态中的人只要看到某个目标词之后就产生厌恶情绪, 然后他们将催眠的人带出催眠状态, 让他们对一系列情境做道德判断, 这些情境如有性关系的表兄妹、受贿的议员、商店小偷、盗书的学生等, 这些情境通过短文描写, 一部分短文中有那个产生厌恶情绪的目标词, 一部分没有, 催眠后的人被要求对这些情境“在道德上错误有多大”和“有多厌恶”做出评价, 结果发现, 那些启动了厌恶情绪的人倾向于更严苛地做出道德判断, 认为这些情境在道德上错误更深(Wheatley & Haidt, 2005)。既然操纵厌恶这种消极情绪可以让人们做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 那么操纵积极情绪是否能让道德判断更为宽松呢?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确有其证据。研究发现, 一组看了5分钟喜剧短片的人比另一组看了5分钟纪录片的人在判断天桥上将胖子推下这一行为是否合适时, 更多地认为这一行为是合适的(Valdesolo & DeSteno, 2006)。不过情绪效价也许并不是道德判断的原因之一, 不同种类的情绪才是影响道德判断的原因, 如欢快情绪会使我们对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的严格程度有所放松, 而提升感这种情绪则有着相反的效果(Strohminger, Lewis, & Meyer, 2011)。直接操纵情绪能够为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提供证据, 除了行为数据, 对比脑损伤患者与正常人也可看作一种操纵的方法。对比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受损伤的患者与正常人在道德判断上的区别, 可以被近似地认为是在操纵情绪。而实际上,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作用已经被绝大多数心理学家所认可, 情绪是我们违反了道德准则后的反应, 情绪
第11期 喻 丰等: 道德困境之困境 1707
使我们做出道德判断, 情绪甚至还能扩大我们道德判断的结果, 它让我们觉得坏人更坏, 情绪使我们已经做出的道德判断更为极端(Bloom, 2010; Pizarro, Inbar, & Helion, 2011)。 3.2 道德判断中认知的作用如何
严格说来, 道德判断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 即使情绪在自动化道德判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一过程也脱离不了广泛意义上认知的含义。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此处讨论的认知指的是有意识的、审慎的、较少受情绪影响的冷加工过程, 更类似于道德推理。
海特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 道德推理的作用不在于做出道德判断, 而在于对道德判断做出事后解释。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会自动化地判断出对错, 然后再为我们的判断去寻找理由和证据, 这个寻找理由的过程就是道德推理。当然研究结果也发现, 人们能很快地判断出兄妹接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但是他们却很难快速地说出理由(Haidt et al., 1993; Haidt, 2001)。同样, 行为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但我们往往不认为自己不知道, 而以为自己知道。在商场里买东西的顾客面对一模一样的袜子多数选择了右边的那双, 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是右利手, 但当问起他们选择那双袜子的原因时, 没有人说得出真正的原因,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给自己的选择找出了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Nisbett & Wilson, 1977)。这说明我们高估了审慎的认知推理过程, 它很多时候就是为我们已经做出的判断和行为去寻求事后解释。不过, 道德推理的作用是否只是次要地做一个事后解释, 这也存在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自动化过程只是处理纷繁复杂信息的一种快速而简便的方式, 受控的审慎加工过程一旦发生, 其作用不是次要地服务, 而是能够主导和更改自动化过程所做出的判断, 比如人能有意识地抵御诱惑, 孩子也能有意识地控制想吃糖这种自动化欲望, 以求获得更大奖赏(Pizarro & Bloom, 2003; Mischel & Ebbesen, 1970)。
当然, 认为审慎认知对道德判断没有作用的学者通常是为了证实另一个结论, 即包含情绪的自动化过程让人们做出道德判断。不过, 自动化的加工过程是否一定要包含情绪在内呢?当然也不一定, 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同样可以是一个冷认知过程, 比如道德启发式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
自动化地根据一定的规则或者道德信念来做出道德判断, 这就是启发式, 例如, “做大多数人做的事” (Laland, 2001; Gigerenzer, 2008)。这一过程也会自动化地发生, 但也无需情绪的参与, 人们此时仅仅是根据一条自己固有的信念来自动化地做出道德判断(Gigerenzer, 2008; Sinnott-Armstrong et al., 2010)。实际上, 有时候这些道德启发式与人类进行经济决策时的启发式如出一辙, 当然人们也会对道德情境进行不含情绪的经济权衡, 如得失分析(cost-benefits analysis) (Bennis, Medin, & Bartels, 2010; Bazerman & Greene, 2010; Bartels & Burnett, 2011)。事实上, 道德判断与经济判断一样, 可能都需要计算结果变量的强度和发生频率, 它们甚至可能共享同样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和经济决策一样,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是活动的预期道德价值判断(如有多少人生还的比例)的指标, 而右前岛叶(right anterior insula)是结果概率的有效指标(Shenhav & Greene, 2010)。
现有研究发现, 做出道德判断还与对道德情境的其他判断有关。这些判断也许是自动化发生的, 但这些判断并没有什么情绪过程参与其中。比如道德走运(moral luck)情境:父亲在澡盆里打满了水, 这时电话来了, 他就出去接电话并让自己两岁的孩子站在澡盆旁边(Young, Nichols, Saxe, 2010)。这个孩子可能自己爬进澡盆中被溺死, 也可能不会, 两个结果中运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先前研究认为在道德走运情境中做出道德判断的首要因素是结果, 也就是人们会做结果论的判断, 但事实上发现并非如此, 人们对父亲信念的判断(他是否知道孩子不听话)要胜过对行为结果的判断(Young et al., 2010)。对道德行为主体信念的判断对最终道德判断作出有着影响, 这提示我们, 做出道德判断时可能会是自动化进行的, 但这个自动化的过程并不一定需要情绪参与其中, 也可以是单纯的认知过程, 如归因。研究发现, 行动和不作为(action ? omission)这一维度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因果归因(causal attribution)来中介的, 而手段和副作用(means ? side-effect)这一维度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则主要是意图归因(intentional attribution)上的差别(Cushman & Young, 2011)。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注射药物让绝症患者安乐死比尽一切可能去试图延缓其生
170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命要更不道德, 而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觉得为了打击敌人士气而屠杀村民比为了炸掉敌人地道而使附近村民被炸死更不道德(Cushman & Young, 而他们造成的结果也有伤害、帮助和中性三种), 那么右侧颞顶联合区(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以及一些左侧颞顶联合区(left 2011)。对道德行为主体的意图的判断也是做出最终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之一。如当道德行为主体的意图都是无辜的时候, 人们会认为意外乱伦的人比意外伤害了别人的人在道德上错误更大; 而当道德行为主体是有意为之时, 人们会认为伤害他人未遂者在道德上所犯的错误要大于乱伦未遂者(Young & Saxe, in press)。对道德行为主体的意图判断除了意外或者是副产品之外, 还包括是否被胁迫。当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 我们会判断那些胁迫他人的个体或者是能自由选择的个体比那些被胁迫的个体更为不道德(Young & Phillips, 2011)。因此对行为意图的判断这种认知过程在道德判断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会发现, 做出道德判断需要各方面判断及信息的整合, 而左右脑区的联合运作则是信息整合的基础, 研究发现, 让胼胝体部分切除和整体切除的患者进行需要言语信息的道德判断任务, 每个患者都只能做结果论道德判断而不能做义务论道德判断(Miller et al., 2010)。这说明要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需要将信念、意图、结果等信息首先整合在一起, 这种能力就是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 即对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的推理。额颞叶型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患者心理理论能力差, 因此其社会认知能力和做出的道德判断均不同于普通人(Gleichgerrcht, Torralva, Roca, Pose, & Manes, 2011)。自闭症患者通常被看作是在社交方面有障碍, 他们也许是在心理理论上和正常人有差别。不过研究发现, 这些人实际上在错误信念(一种心理理论的测量方法)任务上与正常人无异, 但是他们在道德判断上与普通人模式并不相同, 正常人认为有意伤害比无意伤害更不道德, 但自闭症患者认为二者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差别(Moran et al., 2011)。心理理论让人具有道德推理的能力, 而不仅仅是根据行为结果来进行道德判断, 人们会责备伤害他人未遂者, 但会宽恕造成意外伤害的人。由于谴责不道德行为和赞扬道德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维度(Wiltermuth, Monin, & Chow, 2010), 因此如果让实验参与者分别对道德行为主体进行谴责与否或者是赞扬与否的评价(其中道德行为主体的意图有企图伤害、企图帮助和中性三种,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lTPJ)和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神经反应就能反映信念与结果间的交互作用, 无论是做出责备还是赞扬的道德判断, 人们在仅仅依赖道德行为主体的意图做出负性道德判断(要责备或是不赞扬)时, 这些区域的反应都最为强烈(Young, Scholz, Saxe, 2011)。
受到道德判断中情绪研究的冲击, 发展心理学家开始疾呼:“共情、厌恶这类情绪也许是道德的根源, 但心理学家也不应该放弃对审慎思考作用的探讨, 并仍然应该争论人类观念是随着时间如何变化的” (Bloom, 2010)。事实上, 当代道德发展观的学者也确实采取了一个更为温和的观点来看待审慎认知加工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他们认为, 即使成年人确是依靠道德直觉来做快速的道德判断, 但这一道德判断的基础即他们所依靠的信念, 却是儿童期的时候花费巨大代价, 缓慢、审慎、有意识并艰苦习得的(Turiel, 2006)。道德发展观实际上是在退而求其次, 认为快速自动化道德判断的基础也应该是审慎认知加工过程, 他们所谓的信念也可以看作道德启发式, 但是道德启发式观并没有强调这些信念就是早期经验和文化、教育的结果, 这些信念的形成也可能是由于进化适应过程而产生。现有证据表明, 3岁的孩子就已经对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有了直觉性的反感, 而这甚至早于孩子对公平概念的理解(Lobue, Nishida, Chiong, Deloache, & Haidt, 2011)。这表明自动化道德判断的基础也许并不是逐步发展的审慎学习过程, 而是更早出现的情绪过程, 但是这一结果也不能立即否定道德信念有习得的成分。
对审慎认知加工作用最有力的支持来自格林的双加工模型。格林发现, 在是不是捂死自己的孩子以保全大家的生命这个道德困境上, 人们既可以做结果论判断又可以做义务论判断, 但是做决策之时前扣带回皮层(ACC)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这两个特殊的脑区会被激活(Greene et al., 2004)。背外侧前额叶是认知控制的脑区, 而前扣带回皮层会对冲突事件(如Stroop任务)做出反应, 这正说明了这一道德困境产生了情绪与认知的冲突, 而且很显然地可以推论出, 道德困境同
第11期 喻 丰等: 道德困境之困境 1709
时引发了情绪与审慎的认知(Greene et al., 2004; Cushman et al., 2010)。同样, 要确证审慎认知加工的作用, 必须操纵认知。于是研究者们用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作为自变量来观察道德判断的结果, 结果发现, 在同时进行其他任务, 即增加认知负荷的情况下, 人们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的反应时要更长(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双加工理论认为情绪导致义务论道德判断, 而审慎认知导致结果论道德判断, 因此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此观点。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工作记忆容量这种与认知负荷和控制功能高度相关的指标也与道德判断的结果高度相关(Moore, Clark, & Kane, 2008; Moore, Stevens, & Conway, 2011)。不过, 认知负荷的变化虽然改变了做出判断的反应时, 但并未改变最终判断的结果, 这同样又给此结果留下可供商榷之处(Haidt, 2010)。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对情绪的操纵也没有逆转道德判断的结果, 虽然唤起了积极情绪的人会比唤起中性情绪的人做出更多的结果论道德判断, 但这只是基于两组间的比较, 实际上在积极情绪者的判断中, 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不能将人推下天桥)的人数还是占多数(Valdesolo & DeSteno, 2006)。
4 情与理:何去何从
无论各种当代心理学理论如何看待情与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至少心理学家们是在用实验的方法来探讨伦理学问题, 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让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待这些光靠思辨难以解释的问题。虽然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相比起一直以来的思想传统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和数据为各种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使理论并不会建立在单纯的思考之上, 也使理论和假设的说服力剧增。不得不说, 当代心理学将实验方法引入到伦理问题的研究之中已经使我们看到解决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的希望, 使现代道德心理学家们能站在那些伟大哲学家的肩膀上用更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去理解那些早已久远但悬而未决的谜题。
从当代道德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来看, 如皮亚杰和科尔伯格般单纯地只强调道德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已然不可取, 情绪应该在道德判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情绪的作用究竟有多
大?情绪的作用是否能大到可以完全盖过道德推理?道德推理是否完全不能决定道德判断?在这些问题上, 心理学家们仍然存在争议。而解决这些争议的办法无他, 唯有寻找实证证据, 进行心理学实验。为解决这些争议, 解决以下问题应是当务之急:
第一, 道德推理是否只能是做事后解释, 它能否发生于道德判断之前并指导道德判断的结果?即使是道德推理发生在道德判断之后, 那么它是否能扭转道德判断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探查在最初面临道德情境之时, 审慎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否能与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同时发生?或者审慎的认知加工过程一旦发生, 是否是起主导作用?其次, 应当考察人们道德判断发生改变时的情况。如果人们面临某一情境首先做出了某一道德判断, 而其后却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判断, 那我们就应当考察在这样的情形下, 是什么让个体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决策, 特别是考察在这一过程中道德推理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二, 如何更好地操纵情绪与推理过程以观察道德判断的结果?操纵自变量, 控制无关变量来观察因变量的变化是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核心, 也是使我们做出因果推论的首要保障。如果能很好地操纵情绪和审慎认知过程, 也许这一问题能够迎刃而解。生理学指标有可能会作为较为稳定的自变量来进行情绪和审慎认知的操纵, 比如观察脑部受损者和正常人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 但是这是一种比较费时, 也难以直接操控和取样困难的方式。不过随着技术和工具的发展, 我们可以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在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这种可逆损伤方法中, 我们可以主动改变情绪或者是审慎加工过程对应区域的脑功能状态, 使之能作为自变量来为我们服务(Bauer, Leritz, & Bowers, 2003)。
第三, 人的道德判断也许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个体内的过程, 很多情况下, 它依赖于情境。举例来说, 当人们闭上眼睛时, 他们会比睁着眼睛时做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 也会更信任他人(Caruso & Gino, 2011)。同样, 干净与否这一简单的情境变化也能对我们造成影响, 仅仅是自己干不干净就能使我们对同一道德问题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Zhong, Strejcek, & Sivanathan, 2011)。那么
171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我们对于道德判断机制的探讨是否除了情与理这样的个体内过程外, 还应考虑人们所生活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呢?情境到底是影响了情绪还是影响了人们的道德推理过程才使得道德判断发生改变?这些问题依赖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道德判断中的情与理之争的答案终将会在不断的科学实验中浮出水面, 科学的目的就是探寻事实, 它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道德的, Cushman, F., & Young, L. (2011). Patterns of moral judgment derive from nonmoral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Cognitive Science, 35, 1–24.
Cushman, F., Young, L., & Greene, J. D. (2010). Our mutli-system moral psychology: Towards a consensus view. In J. Doris, G. Harman, S. Nichols, J. Prinz, W. Sinnott-Armstrong, S. Stic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ral psycholog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但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道德判断的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 即使美国名校伦理学专业的博士生也不能坚持着他们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则,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居然会受到这些原则出现的顺序效应的影响(Schwitzgebel & Cushman, in press)。因此, 在考虑做出道德判断的关键因素上, 也许没有专家能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可以依靠的只有实验证据。
参考文献
Baron, J. (1994). Nonconsequentialist decisio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7, 1–42.
Bartels, D. M., & Burnett, R. C. (2011). A group construal account of drop-in-the-bucket thinking in policy preference and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50–57.
Bauer, R. M., Leritz, E., & Bowers, D. (2003). Research methods in neuropsychology. In J. A. Schinka & W. F. Velicer (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y, vol. 2: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pp. 289–322).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Bazerman, M. H. & Greene, J. D. (2010). In favor of clear thinking: Incorporating moral rules into a wise cost-benefit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209–212.
Bennis, W. M., Medin, D. L., & Bartels, D. M. (2010).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alculation and moral rules.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 187–202. Bloom, P. (2010). How do morals change? Nature, 464, 490. Caruso, E. M., & Gino, F. (2011). Blind ethics: Closing one’s eyes polarizes moral judgments and discourages dishonest behavior. Cognition, 118, 280–285.
Cohon, R. (2010). Hume's moral philosophy.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0 edition). Retrieved February 22, 2011,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0/entries/hume-moral/
Crain, W. C. (1985).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pp.118-136).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Denis, L. (2009). Kant and Hume on morality.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0 edition). Retrieved February 22, 2011,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09/entries/kant-hume-morality/
Fischer, K. W., & Tangney, J. P. (1995).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nd the affect revolution: Framework and overview. In J. P. Tangney & K. W. Fischer (Eds.),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 psychology of shame, guilt, embarrassment, and pride (pp. 3–22). New York: Guilford.
Foot, P. (1967).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Oxford Review, 5, 5–15.
Gigerenzer, G. (2008). Moral intuition = 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 In W. Sinnott-Armstrong (Ed.), Moral psychology, volume 2: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morality: Intuition and diversity (pp. 1–2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leichgerrcht, E., Torralva, T., Roca, M., Pose, M., & Manes, F. (2011). The rol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moral judgment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Social Neuroscience, 6, 113–122.
Greene, J. D. (2003). From neural "is" to moral "ought": What are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neuroscientific moral psycholog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4, 847–850. Greene, J. D. (2007). 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 In W. Sinnott-Armstrong (Ed.), Moral psychology, vol. 3: 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Emotion,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pp. 35–8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2008).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7, 1144–1154.
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4).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44, 389–400. Greene, J. D., Sommerville, R. B., Nystrom, L. E.,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 293, 2105–2108.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第11期 喻 丰等: 道德困境之困境 1711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814–834.
Haidt, J. (2007).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316, 998–1002.
Haidt, J. (2008). Moralit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65–72.
Haidt, J. (2010). Moral psychology must not be based on faith and hop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182–184.
Haidt, J., & Bjorklund, F. (2008). Social intuitionists answer six questions about moral psychology. In W. Sinnott-Armstrong (Ed.), Moral psychology, volume 2: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morality: Intuition and diversity (pp. 181–21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idt, J. & Kesebir, S. (2010). Morality.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pp. 797–832). Hoboken, NJ: Wiley. Haidt, J., Koller, S. H., & Dias, M. G. (1993). Affect, culture, and morality,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613–628.
Hume, D. (1978).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2nd ed., L. A. Selby-Bigge & P. H. Niddich,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39–1740)
Johnson, R. (2010). Kant's moral philosophy".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0 edition). Retrieved February 22, 2011,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0/entries/kant-moral/
Laland, K. N. (2001). Imitation, social learning, and preparedness as mechanism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n G. Gigerenzer & R. Selten (Eds.),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pp. 233–24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apsley, D. K. (2006). Moral stage theory. In M. Killen & J. D.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p. 37–66).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Lobue, V., Nishida, T., Chiong, C., Deloache, J. S., & Haidt, J. (2011). When getting something good is bad: Even 3-year-olds react to ine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 20, 154–171.
Miller, G. (2008). The roots of morality. Science, 320, 734–737.
Miller, G. A. (2003).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141–144. Miller, M. B., Sinnott-Armstrong, W., Young, L., King, D., Paggi, A., Fabri, M., et al. (2010). Abnormal moral reasoning in complete and partial callosotomy patients. Neuropsychologia, 48, 2215–2220.
Mischel, W., & Ebbesen, E. B. (1970). Attention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329–337.
Moore, A. B., Clark, B. A., & Kane, M. J. (2008). Who shalt not kil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executive control, and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549–557.
Moore, A. B., Stevens, J., & Conway, A. R. A. (201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nsitivity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 predict moral judg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 621–625.
Moran, J. M., Young, L. L., Saxe, R., Lee, S. M., O’Young, D., Mavros, P. L., et al. (2011). Impaired theory of mind for moral judgment in high-functioning autis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 2688–2692.
Nisbett, R. E., & Wilson, T. (1977).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231–259.
Paxton, J. M., & Greene, J. D. (2010). Moral reasoning: Hints and allegations.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2, 511–527.
Pizarro, D. A., & Bloom, P. (2003).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oral intuitions: Comment on Haidt (2001).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197–198.
Pizarro, D. A., Inbar, Y., & Helion, C. (2011). On disgust and moral judgment. Emotion Review, 3, 267–268.
Schwitzgebel, E. & Cushman, F. A. (in press). Expertise in moral reasoning? Order effects on moral judgment in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s and non-philosophers. Mind and Language.
Shenhav, A. S., & Greene, J. D. (2010). Moral judgments recruit domain-general valuation mechanisms to integrate representations of probability and magnitude. Neuron, 67, 667–677.
Sinnott-Armstrong, W., Young, L., & Cushman, F. (2010). Moral Intuitions as Heuristics. In J. Doris, G. Harman, S. Nichols, J. Prinz, W. Sinnott-Armstrong, & S. Stic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ral psycholog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rohminger, N., Lewis, R. L., & Meyer, D. E. (2011). Divergent effects of different positive emotions o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19, 295–300.
Sunstein, C. R. (2005). Moral heuristic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531–573.
Thomson, J. J. (1976). Killing, letting die, and the trolley problem. The Monist, 59, 204–217.
Turiel, E. (2006). Thought, emotio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al processes in moral development. In M. Killen & J. G.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p. 7–35). Mahwah, NJ: Erlbaum.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171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1124–1131. Valdesolo, P., & DeSteno, D. (2006). Manipulations of emotional context shape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476–477.
Wheatley, T., & Haidt, J. (2005). Hypnotically induced disgust makes moral judgments more sever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780–784.
Wiltermuth, S. S., Monin, B., & Chow, R. M. (2010). The orthogonality of praise and condemnation in moral judgm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 302–310.
Young, L., Nichols, S., & Saxe, R. (2010). Investigating the neural and cognitive basis of moral luck: It’s not what you
do but what you know.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1, 333–349.
Young, L., & Phillips, J. (2011). The paradox of moral focus. Cognition, 119, 166–178.
Young, L., & Saxe, R. (in press). The role of intent across distinct moral domains. Cognition.
Young, L., Scholz, J., & Saxe, R. (2011). Neural evidence for “intuitive prosecution”: The use of mental state information for negative moral verdicts. Social Neuroscience, 6, 302?315.
Zhong, C. B., Strejcek, B., & Sivanathan, N. (2011). A clean self can render harsh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859–862.
Dilemma of Moral Dilemmas:
The Conflict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ing in Moral Judgments
YU Feng1; PENG Kai-Ping1,2; HAN Ting-Ting3; CHAI Fang-Yuan1; BAI Yang1,2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 USA) (3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ough moral judgment ranks among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human activities, arguments about the roles of emotion and reasoning play in moral judgment never cease. From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between Hume and Kant to the debates amo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arguments about the power of the situations to neuroscience insights about the brain constraints to human morality, modern psychology has witnessed the paradigm shifts from time to time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and reasoning in moral judgments. We reviewed several competing theories on moral judgment and gave a synthetic view of the roles emotion and reasoning play in moral judgment. We suggest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ontributions in understanding human morality would come from the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moral judgments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involving real individuals with real implications. Methodologically, multi-level and multi-method analysis is much needed. By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situational factors in moral judgments, we may eventually be able to go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emotion and reasoning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human moral judgments. Key words: morality; moral judgment; moral reasoning; emotion; dual-process model
范文五:道德困境
我的道德困境——公交车让座
作为一个大学生外出难免要坐公交车,但是在公交车上的让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要不要让座之间犹豫不决。有时候在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会果断让座,有的时候在自己奔跑了一天很疲劳的时候却不想那么主动的给有需要帮助的人让座。
公交车让座不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具体体现,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 道德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随着历史时代的不同,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涵。公交车让座是从小老师和家长都会教育的乐于助人的美德,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体现。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更有责任传承这一美德。
让座只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谐而倡导的一种美德,应该源自内心,而非法律规定,也没有强制义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照顾老弱病残,公交车上给需要座位的人让座,是社会大力提倡和弘扬的。我想这样的道德困境在生活中是每一个同龄人都会遇到的。
在公交车上,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主动让座,即不会只要见到需要就马上让座,一些人会进行观望后让座,一些人观望完了也不会让座,还有一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迫不得已才让座。在我看来这些情况的出现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心理:心理一:别人不让我也不让。心理二:他离得比我近应该他让而不是我。心理三:有年轻人都不让,我年龄比较大不应该让。心理四: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让座有点显摆。当然,这些心里因素只是少数人所有,一般只有那些素质较低,不让座的人才出现的,但是,这些不良心理容易扩散和蔓延,一旦形成群体心理就会极大影响让座社会公德的实现。每次自己不愿主动让座时就会有这几种心理,
这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内心也在挣扎徘徊。
上小学时老师就经常教育我们在公交车上要主动给需要的人让座,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得很好,那时候我们都有一颗积极的心态,对老师都无比的崇拜,因此对老师赞扬的事我们都会积极去做、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公交车让座的观念还是很强,但由于各种心理因素等是我们不再那么积极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不知而不行原因在于不知,要促进知才能为行打下基础,但是知而不行或知而错行 却反应了一个人素质。
人是富有情感的动物,俗话说“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人性,会关心人,理解人。看到那些白发苍苍、腿脚不便老人我们更应该表现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也会有爷爷奶奶,也希望自己的爷爷奶奶在公交车上可以得到别人的关心和帮助,但首先我们要先学会帮助别人。看到你那些抱着小孩儿或者怀孕的年轻妇女我们也要主动献出爱心,作为一个健康的人,在公交车上还会觉得累觉得不舒服,何况她们还抱着孩子,一定更累,她们真的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同时在给别人提供方便和帮助的时候还会得到别人感谢,这些都美化着我们的心灵,这样的和谐的社会是多么美好。
在公交车让座的社会公德实现的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来传承这一传统美德,尤其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正要步入社会,更有责任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为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惭愧。
每个人都会有老的时候,都会需要这个社会帮助的时候,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年轻的时候多为社会做贡献,多为社会
贡献自己的爱心,创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到自己老的时候这样的充满爱的社会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温暖。
在遇到这样的道德困境后经过自省与反思我觉得我应该积极去传承公交车让座这一美德,为我们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我会积极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尊老爱幼、乐于助人为身边的人带去更多的关心和温暖。
公交车让座只是社会公德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还有许多关于社会公德建设的内容。希望在新时代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通过道德建设和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社会公德意识和道德认知,并把其很好转化为行动,共同创建和谐家园、美好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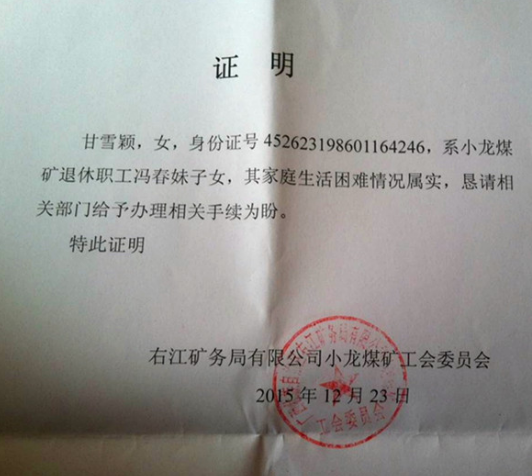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Alwayshere32782496
Alwayshere32782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