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键词:气溶胶、生物恐怖、气溶胶检测
Abstract
Aerosol science is a new science whose development is rapid, and biological aerosol as a kind of aerosol are widely used in environment, medicine, military and terrorist and terro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iological aeros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pplication. Biological aerosol are pathogenic big, strong, large area pollution infectious, low cost, especially to use biological aerosols can cause psychological panic, which is particularly applicable to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or anti-terrorism, biological aerosols detection appears extremely important, sampling,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Key Words: Aerosol, Biological terrorism, Aerosol testing
按生物战剂的性质分类,可分为(1)细菌,包括:炭疽杆菌、鼠疫
杆菌、霍乱弧菌、马鼻疽杆菌、野兔热杆菌、布鲁氏杆菌、军团杆菌等。
(2)病毒,包括::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森林脑
炎病毒、登革热病毒、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等。(3)立克次体,如斑
疹伤寒立克次体和Q热立克次体等。(4)衣原体,如鸟疫(鹦鹉热)衣原体
等。(5)毒素: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6)真菌:如球孢
子菌、组织胞浆菌等#。其中最危险的产品有:(a)炭疽杆(BacillusAntbracis)
或炭疽(anthrax),尺寸范围1—10“m,具有可吸入性、耐药性及致命性;(b)天花病毒(small-pox virus),致命性弱于炭疽但极易传染。(c)肉毒杆菌毒素,来源于一种专性厌氧、革兰氏阳性、可生成孢子的土壤细菌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肉毒是迄今所知毒性最强的毒素。(d)葡萄球菌内毒素B,对过摄食和吸入而传播,但这种气溶胶制剂除非大量摄食或吸入,罕有致使效果。(e)产气英膜梭菌毒素,作为战争和恐怖行动的武器之一,也可能以气溶胶的形式被有效地大量扩散。从理论上讲,大剂量的毒素可迅速使军队和居民致残,致死率不明。(f)蓖麻毒蛋白,从蓖麻子中提取的细胞毒性蛋白,可污染
食物和水源,也可以以气溶胶形式被吸入,恐怖袭击时需要有大量的蓖麻毒蛋白,才能达到扩散毒害的目的[2, 3]。
生为支气管炎。还有一种是过敏性肺炎,肺泡被引起炎症的细胞占据或破坏,若病情持续,将导致肺痨,并使得呼吸功能失调。而星期一症候群其症状也相当复杂,常发生于一天或数天的不上班后,再重新回到工作环境的时候。若工作环境的人数大于三人,症状有可能会互相传染,包括气喘、咳嗽、发烧、肌肉酸痛。这种类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状会维持数小时,通常隔天仍会重复这一症状,其将随着暴露天数的增加而逐渐缓和,长期会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及肺痨[5]。
经历过恐怖事情后,有些人对恐怖和无望产生情感反应,对恐怖事件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反应程度取决于是否会发展成恐怖性神经症或恐惧症。这种病人反应将持续并可致残。恐惧症可以在恐怖事件后立即出现,也可在数周或数月后出现。青少年心身尚处于发育时期,心理脆弱,更易
造成损害。
常见心理障碍有:抑郁发作,焦虑障碍,谵妄与躁狂状态,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致精神障碍,过度换气综合征,自杀行为。抑郁发作包括抑郁、抑郁一狂躁等一组精神障碍。可以出现广泛心境紊乱、精神运动功能失调;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抑郁和情绪高涨是心境障碍情感内容,常有反复发作。发作的表现有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自杀意念或有自杀、自残行为。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6,7]。
用于生物恐怖主义的病原菌的感染途径主要有3种。细菌可以附着在食物上进入肠遭,形成肠性感染;细菌飘浮在空气中,吸入肺部形成吸入性感染;手或
身体外部接触到细菌后形成接触渗透性感染。皮肤性感染的死亡率只有30,,而吸入性的死亡率非常高。
1.喷撒型,喷撒型是借助外力将毒液和气体喷撒出去的一种武器,由于喷撒剂的不同,喷撒器可分为液体喷撒器和气体喷撒器。
液体喷撒式武器的作用原理是,借用一种外来压力将溶解于溶液的试剂喷撒出去,使它形成毒剂气溶胶,较早出出的喷撒式武器有德国的TRGG刺激剂喷射器,该喷射器是由压力刺激剂瓶、携行架和喷射枪3大部分组成。许多国家还研制了各种各样的袖珍式喷射哭器,形状五花八门,有的像香水瓶,有的像钢笔。
气体式喷撒器是把氟利昂、氮气、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等气体混合在
一起,用压力喷入大气中形成气溶胶毒云,这种武器造价昂贵,现在很少采用。
2.投掷型,投掷型武器是种手投式武器,常见的是控暴手榴弹和投掷瓶两类。控暴手榴弹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控暴武器,它又可以分为燃烧型、爆炸型和非燃非爆型三类。燃烧型手榴弹是采用燃烧方式将刺激剂分散到空气中去的一种武器,最早的燃烧型手榴弹是美国的M7催泪手榴弹,它的结构与普通手榴弹的基本相同,是由引信、弹体和主装药三大部分组成。爆炸型控暴手榴弹是采用爆炸方式将刺激剂分散到空气中的一种武器。爆炸型控暴手榴弹与燃烧型的不同之处是主装药是炸药与刺激剂的混合物。巴西图潘化学公司研制和生产的GL—303CN或CS催泪弹是一种典型的爆炸型武器。为了适用于一些易燃物质的地方及密封场所,许多国家还研制了一些非爆非燃型控暴手榴弹。
发射型,发射型警用刺激性控暴武器主要有刺激性枪弹和刺激性榴弹两类。
式采样器和静电沉降式采样器)、?离心式采样器、?光散射采样器、?大容量采样器。
外军生物战剂侦察系统的研制和装备都较早,美军在这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不仅技术领先,而且部队装备也是较为系统的(美军目前拥有三种生物战剂侦察系统:核化生狐式侦察车、生物综合检测系统和联合生物点检测系统。M93AI狐式侦察车是以装甲车为载体的一种高速度、高度机动的核化生侦察系统,它可以在全站场范围内机动侦察,并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和数字通讯系统与指挥部联系,报告战场核化生的污染情
况(这种侦察车主要装备有核化检测和报警设备、生物采样设备、气象监测系统、位置导航系统和数字通讯系统,整个侦察车的操作由3个人完成。
JSLNBCS是一种综合性的NBC侦察车,其主要功能是核化气溶胶的侦察(对生物战剂气溶胶有一定的侦察能力,但不尽如人意。
生物综合检测系统(BIDS)是由美国陆军部研制的一种机动生物战剂侦察、检测和鉴定系统,总体来说,BIDS是由五个部分组成:(1)车辆;(2)掩体;(3)辅助设备;(4)能源;(5)生物检测设备(紫外荧光生物粒子计数器、生物采样器、流式细胞仪和阙值工作站等)。
我们通过联合攻关,研制出了配套的激光粒子分析仪、大流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气溶胶粒子分离浓缩器、免疫金标检测试剂盒、系统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和装备。
近年来,我国国家和军队高度重视生物防御工作,全面加强了规划预案、应急机制、科学研究、专业力量建设等工作,应急管理和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预案编制工作明显加强,专业技术装备与物资储备初具规模,应急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和军队应对生物恐怖等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明显增强,但与生物威胁的严峻形势相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与发达国家的部署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需要重点加强建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生物危害预警机制和评估系统、建立生物危害预警机制和评估系统、建立特需药品、装备的储备和动用机制、加强反生物恐怖特种专业力量建设、加强生物防御相关技术与装备研发、加强日
常安全防范与培训演练[9]。
References:
[1]. 浅谈常见生物恐怖因子类型及释放方式.
[2]. 蒋铭敏与武士华, 现代生物战剂的主要种类和几种重要战剂的危害. 人民军医, 2002(11): .
[3]. Settles, G.S.与王柏懿, 流体力学与国土安全. 力学进展, 2007(4): .
[4]. 魏晓青与王玉民, 生物恐怖的现实威胁与医学对策.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 2008(3): .
[6]. 生物恐怖心理障碍与处理.
[7](A ustralia FE(Engineered mouse virus spurs bioweapon fears(Science,2001,291(5504):585(
生物气溶胶
摘 要
气溶胶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发展迅速,而生物气溶胶作为气溶胶的一种,广泛应用于环境、医学、军事和恐怖与反恐中。本文重点介绍了生物气溶胶——生物战剂在国际反恐中的应用。生物气溶胶致病性大,传染性强、污染面积大、成本低,尤其是使用生物气溶胶造成心理恐慌,特别适用于恐怖组织。对于反恐来说,生物了解气溶胶的释放和检测就显得极为重要。
关键词:气溶胶、生物恐怖、气溶胶检测
Abstract
Aerosol science is a new science whose development is rapid, and biological aerosol as a kind of aerosol are widely used in environment, medicine, military and terrorist and terro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iological aeros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pplication. Biological aerosol are pathogenic big, strong, large area pollution infectious, low cost, especially to use biological aerosols can cause psychological panic, which is particularly applicable to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or anti-terrorism, biological aerosols detection appears extremely important, sampling,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Key Words: Aerosol, Biological terrorism, Aerosol testing
一、 生物气溶胶的概念
气溶胶由固体或液体小质点分散并悬浮在气体介质中形成的胶体分散体系,又称气体分散体系。其分散相为固体或液体小质点,其大小为10-3cm~10-7cm,分散介质为气体。根据分散相的成分可以分为天然气溶胶、生物气溶胶、工业化气溶胶和食用气溶胶。天然气溶胶,云、雾、霭、烟、海盐等。生物气溶胶,微粒中含有微生物或生物大分子等生物物质的称为生物气溶胶(bioaerosol),其中含有微生物的称为微生物气溶胶。工业化气溶胶,有杀虫剂、消毒剂和卫生消毒剂、洗涤剂和清洁剂、蜡、油漆和发胶。 食用气溶胶, 搅拌过的奶油。
生物气溶胶所含的成分相当复杂,有的气溶胶甚至含有几十种元素,主要有微生物,如酵母菌、细菌、病毒等。气溶胶粒子可以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气溶胶影响人体健康最甚者,应属呼吸方面,而粒径大小不同,对呼吸系统的沉积行为也不同,如可呼吸性与不可呼吸性粒径的分界在5 u m左右;但生物气溶胶因为具有生物性,一旦与人体组织或器官接触,便或多或少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所以,不同粒径大小的生物气溶胶均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1]。
二、生物气溶胶(生物战剂)的分类
按生物战剂的性质分类,可分为(1)细菌,包括: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马鼻疽杆菌、野兔热杆菌、布鲁氏杆菌、军团杆菌等。(2)病毒,包括::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登革热病毒、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等。(3)立克次体,如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Q热立克次体等。(4)衣原体,如鸟疫(鹦鹉热)衣原体等。(5)毒素: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6)真菌:如球孢子菌、组织胞浆菌等#。其中最危险的产品有:(a)炭疽杆(BacillusAntbracis)或炭疽(anthrax),尺寸范围1—10“m,具有可吸入性、耐药性及致命性;(b)天花病毒(small-pox virus),致命性弱于炭疽但极易传染。(c)肉毒杆菌毒素,来源于一种专性厌氧、革兰氏阳性、可生成孢子的土壤细菌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肉毒是迄今所知毒性最强的毒素。(d)葡萄球菌内毒素B,对过摄食和吸入而传播,但这种气溶胶制剂除非大量摄食或吸入,罕有致使效果。(e)产气英膜梭菌毒素,作为战争和恐怖行动的武器之一,也可能以气溶胶的形式被有效地大量扩散。从理论上讲,大剂量的毒素可迅速使军队和居民致残,致死率不明。(f)蓖麻毒蛋白,从蓖麻子中提取的细胞毒性蛋白,可污染
食物和水源,也可以以气溶胶形式被吸入,恐怖袭击时需要有大量的蓖麻毒蛋白,才能达到扩散毒害的目的[2, 3]。
三、生物气溶胶(生物战剂)的特点
生物气溶胶的特点:(1)致病性强,传染性大,生物战剂多数为烈性传染性致病微生物,少量即可使人患病。传染性大,在缺乏防护、人员密集、平时卫生条件差的地区,极易传播、蔓延,引起传染病流行。(2)污染面积大,危害时间长,直接喷洒的生物气溶胶,可随风飘到较远的地区,杀伤范围可达数百至数千平方公里。在适当条件下, 有些生物战剂存活时间长,不易被侦察发现。例如炭疽芽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数十年不死,即使已经死亡多年的朽尸,也可成为传染源。其芽胞可以在土壤中存400年之久,极难根除。(3)成本低,有人将生物武器形容为廉价的原子弹。据有关资料显示,以1969年联合国化学生物战专家组统计的数据,当时每平方公里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传统武器为2 000美元,核武器为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而生物武器仅为1美元。(4)生物武器的局限性,易受气象、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烈日、雨雪、大风均能影响生物武器作用的发挥。生物武器使用时难以控制,使用不当可危及使用者本身。生物战剂进入人体到发病均有一段潜伏期,短则几小时,长则一周以上,在此期间采取措施,可减轻其危害[4]。
四、生物气溶胶的危害
由于空气成为最佳媒介,使得生物气溶胶的机动性很大,对其引发的病症也难以捉摸。以类鼻疽(假单胞菌引起的人类与动物的共患病,临床表现多样化,大多伴有多处化脓性病灶)为例,就并非单纯的区域性问题,已超过30个国家发现此种疾病。另外,目前令人闻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属于呼吸道飞沫传染,也属于生物气溶胶。据美国的调查发现,室内生物气溶胶是造成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的主凶,人口中大约3%一5%有此症状。而对大多数澳洲人来说,生物气溶胶导致的哮喘是影响健康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其患病率及死亡率较过去十年高出很多,且明显分布在大都会及其近郊。另外,气溶胶还会引发过敏性鼻炎,导致混合性鼻塞、鼻痒、流鼻水及分泌物过多。若长期鼻塞,对眼睛有刺激感,则可能已受细菌感染至上呼吸道了。支气管哮喘其症状为周期性、反复性的支气管收缩及分泌物过多,造成不同程度的呼吸急促或咳嗽,并且容易被细菌二次感染,衍
生为支气管炎。还有一种是过敏性肺炎,肺泡被引起炎症的细胞占据或破坏,若病情持续,将导致肺痨,并使得呼吸功能失调。而星期一症候群其症状也相当复杂,常发生于一天或数天的不上班后,再重新回到工作环境的时候。若工作环境的人数大于三人,症状有可能会互相传染,包括气喘、咳嗽、发烧、肌肉酸痛。这种类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状会维持数小时,通常隔天仍会重复这一症状,其将随着暴露天数的增加而逐渐缓和,长期会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及肺痨[5]。
经历过恐怖事情后,有些人对恐怖和无望产生情感反应,对恐怖事件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反应程度取决于是否会发展成恐怖性神经症或恐惧症。这种病人反应将持续并可致残。恐惧症可以在恐怖事件后立即出现,也可在数周或数月后出现。青少年心身尚处于发育时期,心理脆弱,更易造成损害。
常见心理障碍有:抑郁发作,焦虑障碍,谵妄与躁狂状态,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致精神障碍,过度换气综合征,自杀行为。抑郁发作包括抑郁、抑郁一狂躁等一组精神障碍。可以出现广泛心境紊乱、精神运动功能失调;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抑郁和情绪高涨是心境障碍情感内容,常有反复发作。发作的表现有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自杀意念或有自杀、自残行为。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6,7]。
五、生物气溶胶的应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等国先后发展出气溶胶的投送方式。生物武器的投送才达到了化学武器的投送水平。80年代后,尽管生物武器的投送手段并没有发生突破,但伊拉克对投送平台做了大规模的探索——利用导弹、火箭、炮弹、无人机等运载工具进行撒播,但没有投入实际应用。近来生物气溶胶越来越多的地用于生物恐怖,用飞机、军舰、炮弹播撒微生物气溶胶的方式进行生物战,使用致病性微生物或毒素等作为恐怖袭击武器,通过一定的途径散布致病性细菌、病毒,造成烈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导致人群失能和死亡,引发社会动荡。
六、生物气溶胶的释放
用于生物恐怖主义的病原菌的感染途径主要有3种。细菌可以附着在食物上进入肠遭,形成肠性感染;细菌飘浮在空气中,吸入肺部形成吸入性感染;手或
身体外部接触到细菌后形成接触渗透性感染。皮肤性感染的死亡率只有30%,而吸入性的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说,生物气溶胶的释放也就是气溶胶的释放,包括化学手榴弹、枪榴弹 、化学喷枪发展到利用飞机、直升机、战车投放或布洒此类战剂,或是利用轻型火箭筒、小型火箭 、迫击炮、火炮等武器来递送和施放此类毒剂弹药。
1.喷撒型,喷撒型是借助外力将毒液和气体喷撒出去的一种武器,由于喷撒剂的不同,喷撒器可分为液体喷撒器和气体喷撒器。
液体喷撒式武器的作用原理是,借用一种外来压力将溶解于溶液的试剂喷撒出去,使它形成毒剂气溶胶,较早出出的喷撒式武器有德国的TRGG刺激剂喷射器,该喷射器是由压力刺激剂瓶、携行架和喷射枪3大部分组成。许多国家还研制了各种各样的袖珍式喷射哭器,形状五花八门,有的像香水瓶,有的像钢笔。
气体式喷撒器是把氟利昂、氮气、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等气体混合在一起,用压力喷入大气中形成气溶胶毒云,这种武器造价昂贵,现在很少采用。
2.投掷型,投掷型武器是种手投式武器,常见的是控暴手榴弹和投掷瓶两类。控暴手榴弹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控暴武器,它又可以分为燃烧型、爆炸型和非燃非爆型三类。燃烧型手榴弹是采用燃烧方式将刺激剂分散到空气中去的一种武器,最早的燃烧型手榴弹是美国的M7催泪手榴弹,它的结构与普通手榴弹的基本相同,是由引信、弹体和主装药三大部分组成。爆炸型控暴手榴弹是采用爆炸方式将刺激剂分散到空气中的一种武器。爆炸型控暴手榴弹与燃烧型的不同之处是主装药是炸药与刺激剂的混合物。巴西图潘化学公司研制和生产的GL—303CN或CS催泪弹是一种典型的爆炸型武器。为了适用于一些易燃物质的地方及密封场所,许多国家还研制了一些非爆非燃型控暴手榴弹。
发射型,发射型警用刺激性控暴武器主要有刺激性枪弹和刺激性榴弹两类。
七、生物气溶胶的采样和检测
生物气溶胶采样不仅要考虑采集效率,更要考虑采样过程对微生物的损伤、采样介质对微生物存活的影响、样品是否易于保存等因素。根据采样器的工作原理,结合采样介质等因素做为分类标准。当前生物气溶腔采样器大致分为7个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可分为若干种。主要有①液体式采样器(冲击式采样器、喷雾式采样器)、②固体式采样器(筛孔式撞击采样器、狭缝式撞击采样器)、③过滤式采样器(不溶性滤材、可溶性滤材)、④沉降式采样器(自然沉降式采样器、热沉降
式采样器和静电沉降式采样器)、⑤离心式采样器、⑥光散射采样器、⑦大容量采样器。
外军生物战剂侦察系统的研制和装备都较早,美军在这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不仅技术领先,而且部队装备也是较为系统的.美军目前拥有三种生物战剂侦察系统:核化生狐式侦察车、生物综合检测系统和联合生物点检测系统。M93AI狐式侦察车是以装甲车为载体的一种高速度、高度机动的核化生侦察系统,它可以在全站场范围内机动侦察,并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和数字通讯系统与指挥部联系,报告战场核化生的污染情况.这种侦察车主要装备有核化检测和报警设备、生物采样设备、气象监测系统、位置导航系统和数字通讯系统,整个侦察车的操作由3个人完成。
JSLNBCS是一种综合性的NBC侦察车,其主要功能是核化气溶胶的侦察.对生物战剂气溶胶有一定的侦察能力,但不尽如人意。
生物综合检测系统(BIDS)是由美国陆军部研制的一种机动生物战剂侦察、检测和鉴定系统,总体来说,BIDS是由五个部分组成:(1)车辆;(2)掩体;(3)辅助设备;(4)能源;(5)生物检测设备(紫外荧光生物粒子计数器、生物采样器、流式细胞仪和阙值工作站等)。
我们通过联合攻关,研制出了配套的激光粒子分析仪、大流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气溶胶粒子分离浓缩器、免疫金标检测试剂盒、系统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和装备。
在研制出的设备和软件的基础上,根据生物防护只标的不同和实际需要,进一步研制开发出机动性能好的生物侦察车,固定式生物气溶胶实时侦察报警系统。生物气溶胶监测技术和装备的研制,突破了网外在牛物粒予监测技术和设备队我}l;4的封锁,填补了我国在生物气溶胶监测技术和装备方面的空白[8]。
近年来,我国国家和军队高度重视生物防御工作,全面加强了规划预案、应急机制、科学研究、专业力量建设等工作,应急管理和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预案编制工作明显加强,专业技术装备与物资储备初具规模,应急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和军队应对生物恐怖等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明显增强,但与生物威胁的严峻形势相比,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与发达国家的部署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需要重点加强建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生物危害预警机制和评估系统、建立生物危害预警机制和评估系统、建立特需药品、装备的储备和动用机制、加强反生物恐怖特种专业力量建设、加强生物防御相关技术与装备研发、加强日
常安全防范与培训演练[9]。
References:
[1]. 浅谈常见生物恐怖因子类型及释放方式.
[2]. 蒋铭敏与武士华, 现代生物战剂的主要种类和几种重要战剂的危害. 人民军医, 2002(11): 第627-629页.
[3]. Settles, G.S.与王柏懿, 流体力学与国土安全. 力学进展, 2007(4): 第614-627页.
[4]. 魏晓青与王玉民, 生物恐怖的现实威胁与医学对策.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 2008(3): 第281-283页.
[5]. 虹雨, 生物气溶胶:室内看不见的污染. 环境, 2003(7): 第30页.
[6]. 生物恐怖心理障碍与处理.
[7].A ustralia FE.Engineered mouse virus spurs bioweapon fears.Science,2001,291(5504):585.
[8]. 孙振海, 生物气溶胶采集技术简介, in 第九届全国气溶胶会议暨第三届海峡两岸气溶胶技术研讨会2007: 中国广东广州. 第 359页.
[9]. 生物气溶胶侦察技术和装备的研制与定型.
生物气溶胶研究进展
生态环境 2006, 15(4): 854-861 http://www.jeesci.com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mail: editor@jeesci.com
生物气溶胶研究进展:环境与气候效应
祁建华,高会旺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环境与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03
摘要:生物气溶胶是大气气溶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气中的扩散、传播会引发人类的急慢性疾病以及动植物疾病。生物气溶胶还可以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并对大气化学和物理过程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也逐渐得到更广泛的关注。生物气溶胶中的几类生物体(如真菌、细菌和藻类)都被鉴别出是有效的云凝结核(CCN ),并在以活性CCN 的形式存在。当生物气溶胶与有机物(OC )碰撞接触时可以改变大气中OC 的化学组成并改变其CCN 特性,从而影响云量并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空气中的微生物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室内空气细菌、病毒、真菌等生物体的监测及来源调查。而对生物气溶胶的准确测定依赖于采样的有效性,为了减少采样中的误差和活性损失,近年来开发了一些具有应用前景的在线采集、分析技术,如自动拉曼光谱、时间飞行质谱等。分布在大气中的生物气溶胶同样可以遵从传输路线进行长距离传输,而且不同类型的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具有不同的浓度和时空分布模式。文章对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在大气生物气溶胶环境效应、样品采集、监测分析以及分布和传输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了较系统的综述。
关键词:生物气溶胶;气候效应;传输
中图分类号:X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75(2006)04-0854-08
大气气溶胶是指大气与悬浮于其中的固体和液体微粒共同组成的多相体系[1]。悬浮于大气的无数固体和液体微粒中,有一些是由陆地和水生环境的生物活动产生的,这些含有微生物或生物大分子等生命活性物质的微粒称之为生物气溶胶。生物气溶胶种类很多,包括空气中的细菌、真菌、病毒、尘螨、花粉、孢子,动植物碎裂分解体等具有生命活性的微小粒子[2-3]。这些有生命活性的物质通常都附着在大气中的非生物颗粒上,如细菌等微生物;也有一些可以单独悬浮于大气中,如粒径很大的花粉颗粒。生物气溶胶粒子的粒径范围很宽,粒径可以从10-3 μm 变化到102 μm [4]。粒子形貌有简单的球体、圆柱体等,也有复杂的不规则形状。Matthias- Maser 等[5]的研究显示,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数浓度相当高,通常维持在大气数浓度的30%左右,而且变化很大(9天内从16%变化到了50%)[6]。而生物气溶胶的质量浓度除了与粒子数量有关外,还取决于它们的粒径,如大气中的花粉粒子虽然数量很少,但是粒径很大,所以具有较高的质量浓度。与非生物气溶胶相比,生物气溶胶的质量浓度一般较小,但有些地区生物气溶胶在总体气溶胶质量浓度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例如,在热带可以占到55%~95%)[7-8]。
生物气溶胶中没有固定的微生物种类。它主要通过土壤尘埃、地面水、植物、动物和人员活动等方式被带入空气,以液态和固态粒子的形式存在,在适宜条件下可以直接在大气中繁殖也可以在沉降基质上繁殖。由于微生物能产生各种休眠体,故可在空气中存活相当长的时期而不致死亡,并可以借助空气介质扩散和传输,引发人类的急、慢性疾病以及动植物疾病[9-11]。除了人体健康效应外,生物气溶胶还可以作为冰核(Ice Nuclei ,IN )和云凝结核(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12-13], 导致云滴和冰晶的形成,从而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并且对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过程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因此,研究生物气溶胶的基本性质、分布、来源、致病机理和气候效应是非常必要的。
1943年美国开始实施“气溶胶感染”计划,60年代全面展开了生物气溶胶的各项研究,70年代其研究从军事领域扩展和深化到了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畜牧业和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近年来,由于公众对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关注,生物气溶胶领域的研究增加很快,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国关于生物气溶胶的研究工作开展于80年代,主要集中于空气中微生物种类、数量的调查[11,14-18]
,但是目前对生物气溶胶性质、环境效应、分布和传输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在生物气溶胶环境效应、采样技术、监测分析、分布和传输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061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40490262)
作者简介:祁建华(1973-),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气环境科学。Tel: +86-532-82031949;E-mail: qjianhua@ouc.edu.cn 收稿日期:2006-02-21
1 生物气溶胶的环境效应
1.1 气候效应
大气气溶胶粒子可以吸收、散射太阳辐射和地面长波辐射,影响地-气辐射平衡,从而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对云的成核作用会影响云的光学特性、云量以及云的寿命,由此对全球气候产生间接影响[19-20]。研究揭示生物气溶胶可以作为冰核和云凝结核[12-13,21],并可以改变其它CCN (如有机气溶胶)的特性而影响云量,进而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此外,生物气溶胶还在大气化学和物理过程中存在潜在的重要作用[22]:1)通过微生物降解影响化学过程;2)通过与大气有机物(OC )碰撞接触改变OC 化学组成,从而诱发OC 作为IN 或CCN 的性能改变;3)促进环境界面化学/雪界面。 1.1.1 成为冰核和云凝结核
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冰核中识别出了生物气溶胶,随后的研究也鉴别出一些细菌类生物气溶胶可以作为有效冰核[23-24],甚至在6 km 的高度还发现了特定的活性冰核细菌[25],它们在接近0 ℃时是活性的(如T IN (假单胞菌属细菌)=-2 ℃)。尽管与大气中的其他气溶胶相比,生物气溶胶的质量较小,但
是它们的密度(~103-104个/m3
)和冰核的数量级大致相同,说明生物气溶胶具有作为有效冰核的潜在重要性。
生物气溶胶中的几类生物体(如真菌、细菌和藻类)以及它们的残体都被鉴别出是有效的CCN [12-13],而且在云中以活性CCN 的形式存在[26]。在水汽过饱和度为0.07%~0.11%时,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Micrococcus agilis , Mycoplana bullata , Brevundimonas diminuta ) 以活化CCN 存在[12],细菌细胞外表面的化学组成、结构和亲水性对CCN 活性起着重要作用。
云中生物气溶胶的数浓度随高度和位置的不同而略有不同。1997年春季在奥地利Mt.Sonnblick 3106 m )云水中细菌的平均数浓度约为1500 cell·mL -1 [26],1999年和2000年春季在奥地利Mt.Rax (海平面上1644 m) 云水中的平均数浓度大约是2.0?104 cell·mL -1 [26]。云中细菌的空气等效浓度估计为5.9?103 cell·m -3 [27]。该值明显低于单位体积的云滴数目(2.0?108/m3),也比在0.28%过饱和度下的CCN 浓度((1.0~2.0)?108/m3)要低[28]。因此Sattler 等[26]认为空气中的细菌类不是CCN 的重要来源,他们根据细菌碳含量转换因子计算出的细菌质量仅占有机碳的0.01%。然而,最近的研究[29]显示细胞粒子(含蛋白质的)是大气气溶胶中重要的一部分,约为1000 Tg·a -1,而海盐气溶胶和矿物质气溶胶分别是3300 Tg·a -1和2000 Tg·a -1。需要注意
的是,目前对形成有效生物气溶胶CCN 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尚不了解,除细菌外,其他类型的生物气溶胶(如花粉、病毒、真菌)在CCN 形成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1.2 对其它类型CCN 特性的影响
生物气溶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们自身可以作为CCN 和IN ,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它CCN (如有机气溶胶)特性的重要作用。一旦具有不同粒径和密度的粒子的有机化学组成发生改变,它们的CCN 特性也会受损。
大气中的有机气溶胶是形成云凝结核和冰核的一类重要物质,也是全球CCN 预算中重要的一部分。二羧酸(DCA )是有机气溶胶中的一类主要物质,大气边界层中的DCA 可以被细菌和真菌转化,目前已经在7种不同的DCA 化学转变中观察到了大气真菌的存在[30]。化学转化产物中,一些是无毒或低毒性的化合物,如乙酰胺、乙酸、丁酸和丙酸,还有一些是高毒性或致癌物质(如曲菌酸)。同时还检测出了挥发性化合物如多环芳烃或杂环化合物,这表明新沉降的DCA 通过微生物过程可被循环返回大气中。DCA 并不是能被空气微生物降解的唯一一类物质,生物气溶胶还可以转化其他大气可测有机官能团,真菌可以引发大气中活性OC 的微生物降解,不同的真菌具有不同的降解速率[21]。有机物的降解寿命变化很大,依赖于所给定的微生物以及试验因子如pH 和温度[30-31]。研究还发现在有机溶液中空气微生物的存在可以改变OC 的组成。这说明除了微生物降解外,生物气溶胶在与有机物碰撞接触时可以通过细胞溶解和解吸过程改变大气中有机物的化学组成以及非生物OC 的CCN 特性。因此,生物气溶胶,特别是细菌和真菌在大气OC 化学转变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目前有关生物气溶胶对大气物理、化学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影响效应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其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的了解并不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1.2 空气质量效应
近年来,国外比较重视生物气溶胶的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室内空气细菌、病毒、真菌、花粉和噬菌体的监测及来源的调查和治理等方面。Kalogerakis 等[32]调查了雅典和希腊其它一些地区的室内空气质量,同时测定了生物气溶胶浓度,结果显示生物气溶胶是室内空气污染表征体系的一部分,对于评价空气污染的致病性和过敏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室内生物气溶胶可以来自室外空气源或室内
(包括光化学),如空气(海平面上
源,如居住者和作为微生物寄主的建筑材料。被水浸泡过的建筑材料中,细菌和真菌的生长是人体健康的一个潜在危害。Fabian 等[33]发现洪灾恢复后的住宅内空气中微生物的水平要显著高于非受灾住宅,大多能高2~3个数量级,生物气溶胶粒子数平均占到受灾住宅室内粒子总数的52%;受到洪水影响的建筑材料是高浓度生物气溶胶的持续来源,也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室内的家用设备如空调器和加湿器中也容易孳生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成为室内空气微生物的潜在污染源。Law 等[34]研究了香港办公建筑物内生物气溶胶的分布,结果显示空调系统不能有效过滤生物气溶胶。鉴于2001年发生的“炭疽热信件”事件,Ho 和Duncan [9]以Bacillus subtilis globigii孢子模拟炭疽热病毒,研究了含病毒信封产生生物气溶胶的情况,给出了相关的显著气溶胶剂量评估值以及致死剂量值,可用于模型评价空气中微生物的危害性。
空气中的微生物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目前制定的空气质量指数和污染物暴露水平主要是以化合物和颗粒物来定义的,有关生物气溶胶的允许暴露水平和相关规定非常缺乏。在美国,不论环保局(EPA )还是国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ion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 )目前都没有提出生物气溶胶的浓度限值[33]。为了更全面、系统地评价空气质量、保障人体健康,制定出生物气溶胶的允许浓度水平是非常必要的,这依赖于对空气中生物气溶胶的深入研究。
2 生物气溶胶采样和监测
生物气溶胶采样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其活性。大气中微生物活性的主要风险因子是脱水、紫外辐射、温度,还有气体和污染物的行为等。总体上来说,生物气溶胶的存活主要取决于停留时间。在粒子的收集和沉降过程中,微生物会由于机械压力和脱水而失去发育能力。测量得到的微生物浓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样技术和分析方法。生物采样器主要依据撞击、碰撞、过滤等机理采样,因此可用不同的物理采集效率表征。人们常常重视采样过程中收集到的微生物的数量,却忽略了它们的生存能力[35]。因此,Mandrioli [36]建议将采样器的采样效率和样品的生物有效性区分开来,后者可以表述为在采样后仍然存活的粒子的百分率。
目前已经开发了很多种收集生物气溶胶的采样器:单级或多级撞击式采样器,离心式采样器,液体冲击式采样器,过滤式采样器等,但是并没有生物气溶胶户外监测的标准方法[37]。大多数采样器允许将微生物直接采集在琼脂介质上,便于采样后
在合适的条件下进行培养,从而确定微生物群落。用此方法测定得到的可培养微生物的浓度(细菌,真菌) 以每立方米空气中群落形成单元(Colony Forming Units,CFU/m3)表示。但是这种琼脂采样器存在一些缺陷[37]:1)由于采样器不是以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所以重现性较差;2)由于菌落重叠产生较大的计数误差;3)这种方法测定到的只是生命活性物质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环境生物体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不到1%)可以在琼脂上培养生长。
鉴于琼脂采样器的缺点,为了保证样品的采集效率和生物活性,研究者们对常用的几类采样器的采集效率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开发设计了一些新型采样器。Ambroise 等[38]认为Bioimpacteur 100-08、MAS 100、二阶Andersen 撞击式采样器和离心撞击式采样器在采集可培养微生物的效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 =0.1)。但Li 和Lin [39]指出在低浓度生物气溶胶环境中,惯性撞击式采样器要比营养琼脂作为采集面的固体撞击类采样器和过滤阻留类采样器要更适用,并评估出Andersen l-STG 采样器的微生物存活率要高于MAS-100和Burkard 采样器。而Agranovski 等[40]发现用紫外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UV-APS )测得的生物气溶胶浓度要高于AGI-30和6阶Andersen 采样器,这说明传统的方法耗时且低估了大气中存在的微生物[41]。钟嶷等[42]的研究显示撞击法采集空气细菌总数受环境因素影响小、精确度较好,一般情况下可优先采用,而沉降法测定结果精确度较差,适宜在空气流速小且稳定、空气洁净度高、需要较长采样时间(8~30 min) 的环境采用。Sahu 等 [37]开发了一种采集生物气溶胶的静态水表面采样器,该采样器可以定量测定生物气溶胶沉降速率而且不需要在测量之前进行预先培养。
生物气溶胶的有效采集是准确测定生物气溶胶浓度、了解其性质和影响效应的基本前提和保障。现有的大多数采样技术提供的是“可培养”类生物气溶胶的信息,这些只是生物气溶胶总体中的一小部分。为了减少生物气溶胶在采样过程中的误差和活性损失,近年来,开发了一些具有应用前景的在线采集、监测生物气溶胶的分析技术[43-45]。
Laucks 等[46]提出了运用自动拉曼光谱化学表征划分生物气溶胶的方法,同时测定了不同花粉颗粒的空气动力学粒径和密度。Angelo 等[47]开发了从大气气溶胶中快速收集监测生物物质的制备测定技术,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模型预测了未知测试样品中细菌种类的分类。Hairston 等[48]开发了可以根据粒子的空气动力学粒径、特征激发和发射荧光波长测量单个生物气溶胶粒子的仪器,该仪器具有
(
空气动力学粒径分级装置,可以实时测定生物气溶胶粒子的分布特征,特别是空气动力学粒径在0.5到10 μm 之间的粒子。UV-APS 系统可以将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粒径在0.5到15 μm 之间的微生物(诸如细菌和真菌)和普通的尘土粒子分开,并在一分钟内测出它们的浓度和粒径分布,对大气细菌特别灵敏[41]
。而时间飞行质谱(Time-of-fight mass spec-trometer ,ATOFMS) 可以实时分析单个生物气溶胶粒子,该系统对于单个细菌和孢子的鉴定具有很高的应用前景,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分辨率和谱图的精度[49]。
由上可见,目前虽然开发了一些有应用前景的测定生物气溶胶的先进技术,如时间飞行质谱、自动拉曼光谱等,但这些技术所能测定的生物气溶胶的粒径范围是有限的,能够准确测定较宽粒径范围内的生物气溶胶的方法仍有待开发。
3 生物气溶胶分布和传输
与非生物气溶胶一样,悬浮于大气中的生物气溶胶同样受到重力和空气湍流的作用力,不同类型的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具有不同的浓度和时空分布模式。但现有文献中,生物气溶胶的全球信息非常缺乏,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类调查的重要性。
不同地区生物气溶胶的浓度分布特征也不尽相同,有研究者[50]认为生物气溶胶浓度是通量输送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南京市夏季细菌和真菌的平均浓度都高于春季;春、夏两季细菌和真菌的平均浓度都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少;两个季节大气细菌以革兰氏阳性菌占绝对优势[51]。北京市夏季空气中革兰氏阳性菌明显多于革兰氏阴性菌,约占70%~85%,其中阳性球菌占总数的占35%~45%[52]。而青岛市空气中不仅有陆源微生物还有海洋微生物,陆源微生物污染较重,有较强地向滨海区扩张的势头[53]。北京市夏季空气细菌、空气真菌和空气放线菌的粒度分布特征各不相同,没有显著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54]。空气细菌呈偏态分布,大于2.0 μm 的粒子约占总数的80.0%;空气真菌呈对数正态分布,1.0~6.0 μm 的粒子约占70.0%;空气放线菌粒度分布与正态分布恰好相反,大于8.2 μm 和小于1.0 μm 的粒子约占60.0%。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秋季大气颗粒中,在2~10 μm 的生物气溶胶中真菌孢子占大多数,气溶胶计数占总体大气颗粒物质量的5%~10%[55]。Borodulin 等[56]分析了机载试验室在西西伯利亚南部0.5, 1, 1.5, 2, 3, 4, 5.5和7 km高度获得的生物气溶胶浓度的一些物理特征。总体蛋白质气溶胶的浓度遵循连续统计学规律,可培养微生物气溶胶的浓度遵循离散统计学规律,小波分析显示对流层生物气溶胶的浓度变化主要取决于典型
的季节过程。
分布在大气中的生物气溶胶可以像沙尘粒子一样遵从传输路线进行长距离传输。有研究[57]发现,附着在撒哈拉沙尘上的微生物可以长距离传输越过大西洋。沙尘是对流层气溶胶的主要成分,据估计全球每年进入大气的沙尘达1000~3000 Mt ,约占对流层气溶胶总量的一半。目前有关沙尘的研究[58-68]主要集中在沙尘暴的成因、运移以及降尘矿物组分方面,但是对沙尘粒子所携带的微生物及其生态效应的研究却很缺乏。Yeo 等[69]研究了2000年春季在韩国瑞山沙尘天气中收集的沙尘颗粒和真菌孢子,发现大多数沙尘粒子主要由粒径为5 μm 的颗粒组成,同时在沙尘粒子上识别出四类真菌孢子,研究显示在沙尘天气期间大气环境中主要悬浮着一些细粒径的真菌孢子。吴东辉等[70]对2000年4月5日至7日袭击我国大部分地区并波及到长春市的沙尘湿沉降中的细菌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泥雪”样品中需氧性细菌以球菌和杆菌为主,未发现致病菌存在,杂菌数量及种类很多。
可见,沙尘暴这种快速、大范围和远距离的沙尘物质输运在造成非生物大气污染(如重金属)的同时,可能导致生物体(包括细菌类) 的迁移和侵入。所以,沙尘暴在运移的过程中携带的生命活性物质值得重视。
生物气溶胶粒子中,有一些是由水环境的生物活动产生的。研究显示,源于波浪破碎和飞沫的海洋气溶胶同样含有活性物质,海洋气溶胶粒子可以大到足以含有微生物等活性物质(如1~20 μm ),甚至可以从源地被传输到几万公里以外[71],并能在湿度足够高时(70%以上)保持液态。海洋气溶胶的形成是细菌和病毒通过海-气界面传输的一个主要传播媒介。Aller 等[72]发现从海洋表层到海洋微表层的传输中,细菌与病毒富集了15~25倍,然后通过海洋气溶胶进入到了大气中。海洋气溶胶中的大部分微生物深含在有机粒子中,其中有较多的受损和活性降低的细菌细胞。微表层是微生物从水体进入大气的主要来源,雾化是细菌长途传播的一个潜在重要机理,可能与细菌的全球性分布相关[72]。
鉴于长距离输运的生物气溶胶会将外来侵入微生物带入沉降地区,为了预防外来侵入微生物对本地生态系统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借助大气模型准确预测远源生物气溶胶的传输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要求了解传输过程中的动力学,还要了解微生物地理源和汇的时空环境特征。有研究者[73]认为只有将物种的生活史和生态系统的生物气候学联系起来才能了解源生态系统的动力特征,并用于大气参数化模型以预测空气中的生物流。同时也需要和
气象学科合作,并了解大气微生物传输通道。而且模型将最终评价生物气溶胶对大气化学和物理是否有显著贡献[22]。Teptin 等[74]调查了地球大气中生物气溶胶粒子的行为,研究了粒子传输过程中空间分布的局部机理,描述了生物气溶胶粒子的时空分布模型。
4 研究展望
虽然目前对生物气溶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认识,但生物气溶胶的来源有时难以识别,主要是由于其来源多而分散并且难以鉴别,另外还受到气象条件的明显影响。生物气溶胶的性质研究主要集中于颗粒所含微生物的调查,但对其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尚不深入,对化学成分如何影响其CCN 或IN 特性以及化学转化的动力学和机理并不了解。可见,对生物气溶胶的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其来源、转化、传输、流行疾病传播机理和气候效应作用机理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下述问题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1)生物气溶胶对大气过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作为有机气溶胶中独特的一类,生物气溶胶对大气物理、化学过程、全球气候变化存在着潜在的重要影响,但目前对其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尚不清楚。
(2)生物气溶胶与人类和植物流行疾病的关系。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扩散、传播会引起人类急性和慢性疾病以及动植物疾病的流行传播。2003年3月全球受到非典型性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 ,SARS) 的威胁,可是对SARS 是否借助空气传播(飞沫核和气溶胶粒子)存在很大争议,一方面是人们对这种新发疾病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缺乏对生物气溶胶与疾病流行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造成的。
(3)生物气溶胶的源、汇及转化。生物气溶胶种类丰富、来源复杂,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进行长距离传输并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相应的转化,但目前对不同类别生物气溶胶的源、汇和转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深入。
(4)生物气溶胶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及评价因子。目前有关生物气溶胶的允许暴露水平的相关规定非常缺乏。为了更全面、系统地评价空气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研究生物气溶胶对大气质量的影响以及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5)生物气溶胶的时空分布规律。已有的研究揭示不同类型的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具有不同的浓度和时空分布模式,目前对生物气溶胶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但是其全球分布信息非常缺乏。 (6)生物气溶胶输运、沉降过程控制机理。生
物气溶胶可以长距离传输,并会将外来侵入微生物带入沉降地区,对本地生态系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但是目前对生物气溶胶的输运、沉降过程控制机理缺乏了解。
(7)人类活动对生物气溶胶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当前随着各种生物杀虫剂、城市污水微生物处理等微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人为因素造成的进入空气中微生物成分、数量逐渐增多。这些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生物气溶胶的形成,又会如何影响其在大气中的演变?
参考文献:
[1]
王明星. 大气化学[M]. 2版.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9: 166. WANG M X. Atmospheric chemistry[M]. 2nd ed.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1999: 166. [2]
胡家骏, 周群英.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128-131.
HU J J, ZHOU Q 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biology[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8: 128-131. [3]
章澄昌, 周文贤. 大气气溶胶教程[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5: 12. ZHANG C C, ZHOU W X. Course of Study Atmospheric Aero-sol[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1995. [4] GUEST EDITORIAL. Measure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ioae-rosols[J]. Aerosol Science, 2005, 36:553-555.
[5]
MATTHIAS-MASER S, JAENICKE R. Size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biological aerosol particles with radii > 0.2 mm in an urban/rural in-fluenced region[J]. Atmospheric Research, 1995, 39:279-286. [6]
WHITE C C, KENNY C M, JENNINGS S G. A study of marine and continental bioaerosol in the west of Ireland[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9, 30: S809-810. [7]
ARTAXO P, MAENHAUT W, STORMS H, et al. Aerosol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for the Amazon Basin during the wet season[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90, 95(D10): 16971-16985. [8]
ARTAXO P, STORMS H, BRUYNSEELS F, et al. Composition and sources of aerosols from the Amazon basin[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88, 93(D2):1605-1615. [9]
HO J, DUNCAN S. Estimating aerosol hazards from an anthrax letter[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701-719.
[10] LEE N, HUI D, WU A, et al .A major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Hong Kong[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3, 348: 1986-1994.
[11] 郁庆福. 现代卫生微生物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365-402.
YU Q F. Modern Sanitary Microbiology [M]. Beijing: Peop 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5.
[12] BAUER H, GIEBL H, HITZENBERGER R, et al.. Airborne bacteria
as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03, 108: AAC2/1–AAC2/5.
[13] FRANC G D, DEMOTT P J. Cloud activation of airborne Erwinia
carotovora cells[J]. 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1998, 37: 1293- 1300.
[14] 陈皓文. 张家界、韶山和衡山空气微生物粒子沉降量分析[J]. 国
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3, 2: 54-56.
CHEN Haowen. Analysis of air-borne microbial particle precipita-tion above Zhang Jiajie, Shaoshan and Hengshan[J]. Territory &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2003, 2:54-56.
[15] 陈皓文, 洪旭光. 中国南极长城站室内空气微生物状况[J]. 应用
与环境生物学报, 2000, 6(1): 90-92.
CHEN Haowen, HONG Xuguang. Situation on indoor airborne mi-crobes of Chinese great wall station, Antarctica[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Biology, 2000, 6(1): 90-92.
[16] 陈皓文. 吐鲁番市空气微生物浓度状况[J]. 干旱环境监测, 2003,
17(4): 211-214.
CHEN Haowen. The Status of concentration of air microorganism in Tulupan City[J]. Ari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2003, 17(4): 211-214.
[17] 巨天珍, 索安宁, 田玉军, 等. 兰州市空气微生物分析[J]. 工业安
全与环保, 2003, 29(3): 17-19.
JU Tianzhen, SUO Anning, TIAN Yujun, et al. Analysis on aerobi-ologia in Lanzhou[J]. Industri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3, 29(3): 17-19.
[18] 张晟, 郑坚, 付用川, 等. 重庆市城区空气微生物污染及评价[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2, 19(3): 231-233.
ZHANG Sheng, ZHENG Jian, FU Yongchuan, et al. Air pollution by microorganism 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nd its evaluation[J]. J Environ Health, 2002, 19(3): 231-233.
[19] HUDSON J G.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J]. 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1992, 32: 596-607.
[20] LOHMANN U, LESINS G. Stronger constraints on the anthropo-genic indirect aerosol effect[J]. Science, 2002, 298: 1012-1016. [21] SUN J M, ARIYA P A. Atmospheric organic and bio-aerosols as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A review[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6, 40: 795-820.
[22] ARIYA1 P A, AMYOT M. New Directions: The role of bioaerosols
in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 1231-1232
[23] MAKI L R, GALYAN E L, CHANG-C M, et al. Ice nucleation
induced by Pseudomonas syringae[J]. Applied Microbiology, 1974, 28: 456-459.
[24] VALI G, CHRISTENSEN M, FRESH R W, et al. Biogenic ice nuc-lei, Part: Bacterial sources[J].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1976, 33: 1565-1570.
[25] LINDEMANN J, CONSTANTINIDOU H A, BARCHET W R, et al.
Plants as sources of airborne bacteria including ice nucleation active bacteria[J]. Applie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1982, 44: 1059-1063.
[26] SATTLER B, PUXBAUM H, PSENNER R. Bacterial growth in
supercooled cloud droplets[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1, 28: 239-242.
[27] BAUER H, KASPER-GIEBL A, LOFUND M,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bacteria and fungal spores to the organic carbon content of cloud water, precipitation and aerosols[J]. Atmospheric Research, 2002, 64: 109-119.
[28] ROSS K E, PIKETH S J, BRUINTJES R T, et al. 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in CCN distribution and the aerosol-CCN relationship over southern Africa[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03, 108: 8481-8498.
[29] JAENICKE R. Abundance of cellular material and proteins in the
atmosphere[J]. Science, 2005, 308: 73.
[30] ARIYA P A, NEPOTCHATYKH O, IGNATOVA O, et al. Microbi-ological degradation of atmospheric organic compounds[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2, 29: 34/1-34/4.
[31] ARIYA P A, AMYOT M. Bioaerosols: impact on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atmosphere[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 1231-1233.
[32] KALOGERAKIS N, PASCHALI D, LEKADITIS V, et al. Indoor air
quality: bioaerosol measurements in domestic and office premise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 751-761.
[33] FABIAN M P, MILLER S L, REPONEN T, et al. Ambient bioaero-sol indices for indoor air quality assessments of flood reclamation[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 763-783.
[34] LAW A K Y, CHAU C K, CHAN G Y S. Characteristics of bioae-rosol profile in office building in Hong Kong[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01, 36: 527-541.
[35] GRIFFITHS W D, DECOSEMO G A L. The assessment of bioaero-sols: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4, 25 (8):1425-1458.
[36] Mandrioli P. Basic aerobiology[J]. Aerobiologia, 1998, 14: 89-94. [37] SAHU A, GRIMBERG S J, HOLSEN T M. A static water surface
sampler to measure bioaerosol deposition and characterize microbial community diversity[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639-650.
[38] AMBROISE D, GREFF-MIRGUET G, G?RNER P, et al. Mea-surement of indoor viable airborne bacteria with different bioaerosol samplers [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9, 30:.S699-S700. [39] LI C S, LIN Y C. Sampling performance of microbial impactors for
bacterial bioaerosol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8, 29: S50l-S502.
[40] AGRANOVSKI V, RISTOVSKI Z, BLACKALL P, et al. Real-time
detection of bioaerosols at a piggery [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0, 31: S739-S740.
[41] MILLER S, Cheng Y S, Macher J M. Preface to bioaerosol special
issue: guest editorial [J].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9, 30:93-99.
[42] 钟嶷, 郭重山, 李小晖, 等. 自然沉降法和撞击法在空气细菌总
数测定中的应用和比较[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4, 21(3): 149-152.
ZHONG Yi, GUO Chongshan, LI Xiaohui, et al. Application and comparison study of natural precipitation Method and impacting method for measurement of bacterial count of ai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4, 21(3): 149-152.
[43] AGRANOVSKI V, RISTOVSKI Z, HARGREAVES M, et al.
Real-time measurement of bacterial aerosols with the UVAPS: per-formance evaluation[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3, 34: 301-317.
[44] SENGUPTA M L, LAUCKS N, DILDINE E, et al. Bioaerosol cha-racterization by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 651-664.
[45] AGRANOVSKI V, RISTOVSKI Z D. Real-time monitoring of
viable bioaerosols: capability of the UVAPS to predict the amount of individual microorganisms in aerosol particle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665-676.
[46] LAUCKS M L, ROLL G, SCHWEIGER G, et 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RAMAN) characterization of bioaerosols-pollen[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9, 30: S145-146.
[47] ANGELO J M, KENT J V, TED L H. Rapid detection of taxonomi-cally important fatty acid methyl ester and steroid biomarkers using in situ thermal hydrolysis/methylation mass spectrometry (THM-MS): implications for bioaerosol detection[J]. Journal of Analytical and Applied Pyrolysis, 2001, 61: 65-89.
[48] HAIRSTON P P, HO J, QUANT F R. Design of an instrument for
real-time detection of bioaerosols using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particle aerodynamic size and intrinsic fluorescence[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7, 28(3): 471-482.
[49] VAN WUIJCKHUIJSE A L, STOWERS M A, KLEEFSMAN W A,
et al.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sation aerosol time-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the analysis of bioaerosols: development of a fast detector for airborne biological pathogen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 677-687.
[50] 陈铭夏, 金龙山, 孙振海, 等. 生物气溶胶浓度、通量及环境因素
的影响[J]. 自然科学进展, 2001, 11: 939-944.
CHEN Minxia, JIN Longshan, SUN Zhenhai, et al. The influence of bioaerosol concentration, flux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J]. Natural Science Progress, 2001, 11: 939-944.
[51] 陈梅玲, 胡庆轩, 徐秀枝, 等. 南京市大气微生物污染情况调查
[J]. 中国公共卫生, 2000, 16(6): 504-505.
CHEN Meiling, HU Qingxuan, XU Xiuzhi, et al. Investigation on atmospheric bioaerosol pollution in Nanjing[J]. China Public Health, 2000, 16(6):504-505.
[52] 方治国, 欧阳志云, 胡利锋, 等. 北京市夏季空气微生物群落结
构和生态分布[J]. 生态学报, 2005, 25(1): 83-88.
FANG Zhiguo, OUYANG Zhiyun, HU Lifen, et 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airborne microbes in summer in Beijing[J].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5, 25(1): 83-88.
[53] 陈皓文. 青岛空气微生物状况的测定[J]. 山东科学, 2003, 16(1):
9-13.
CHEN Haowen. Determination on condition of air-borne microbes above Qingdao[J]. Shandong Science, 2003, 16(1): 9-13.
[54] 方治国, 欧阳志云, 胡利锋, 等. 北京市夏季空气微生物粒度分
布特征[J]. 环境科学, 2004, 25(6):1-5.
FANG Zhiguo, OUYANG Zhiyun, HU Lifen, et al. Granularity dis-tribution 0f airborne microbes in summer in Beij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4, 25(6): 1-5.
[55] GLIKSON M, RUTHERFORD S, SIMPSON R W, et al. Micro-scopic and submicron components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uring high asthma periods in Brisbane, Queensland, Australi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5, 29(4): 549-562.
[56] BORODULIN A I, SAFATOV A S, SHABANOV A N, et al.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ion fields of tropospheric bioaerosols in the South of Western Siberia[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 785-800.
[57] GRIFFIN D W, GARRISON V H, HERMAN J R, et al. African
desert dust in the Caribbean atmosphere: microbiology and public health[J]. Aerobiologia, 2001, 17: 203-213.
[58] GAO Y, ARIMOTO R, DUCE R A,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dust and its deposition to the China Sea[J]. Tellus, 1997, 49B: 172-189.
[59] OFFER Z Y, GOOSSENS D. Ten years of aeolian dust dynamics in
a desert region (Negev desert, Israel): analysis of airborne dust con-centration, dust accumulation and the high-magnitude dust events[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01, 47: 211-249.
[60] GOUDIE A S, MIDDLETON N J. Saharan dust storms: nature and
consequences[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01, 56: 179-204. [61] NATSAGDORJ L, JUGDER D, CHUNG Y S. Analysis of dust
storms observed in Mongolia during 1937–1999[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3, 37: 1401-1411.
[62] XUAN J, SOKOLIK I N, HAO J F,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ources of atmospheric mineral dust in East Asi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 6239-6252.
[63] WANG S G, WANG J Y, ZHOU Z J, et 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kinds of dust storm events in Chin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5, 39: 509-520.
[64] 赵琳娜, 孙建华, 赵思雄.一次引发华北和北京沙尘(暴) 天气起沙
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J]. 气候与环境研究, 2002, 7(3): 279-294. ZHAO Linna, SUN Jianhua, ZHAO Sixiong.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ust emission in North China[J].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 Chinese), 2002, 7(3): 279-294.
[65] 陈洪武, 王旭, 马禹.塔里木盆地局地和区域性强沙尘暴天气过
程研究[J].中国沙漠, 2003, 23(5): 533-538.
CHEN Hongwu , WANG Xu, MA Yu.A study on the local and re-gional strong sandstorm process in Tarim Basin[J].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in Chinese), 2003, 23(5):533-538.
[66] 方小敏, 韩永翔, 马金辉, 等.青藏高原沙尘特征与高原黄土堆积:
以2003-03-04拉萨沙尘天气过程为例[J].科学通报, 2004, 49(11):1084-1090.
FANG Xxiaomin, HAN Yongxiang, MA Jinhui, et a1.Dust storms and loess accumulation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 case study of dust event on March 4, 2003 in Lhasa[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4, 49(9): 953-960.
[67] 韩永翔, 方小敏, 宋连春, 等. 塔里木盆地中的大气环流及沙尘
暴成因探讨: 根据沙漠风积地貌和气象观测重建的风场[J]. 大气科学, 2005, 29(4): 627-635.
HAN Yongxiang, FANG Xiaomin, SONG Lianchun, et al. A Study of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Dust Storm Causes of Formation in the Tarim Basin: The Restructured Wind Field by Shapes of Dune an d Observed Prevailing Wind[J]. Chinese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2005, 29(4): 627-635.
[68] 谢远云, 何葵, 康春国. 哈尔滨市特大沙尘暴沉降物的粒度分布及
意义[J]. 中国地质, 2005, 32(3): 502-506.
XIE Yuanyun, HE Kui, KANG Chunguo. Grain-size distribution of fall-outs of an exceedingly large dust storm in Harbin City and its implications[J]. Geology In China, 2005, 32(3): 502-506.
[69] YEO H G, KIN J H. SPM and fungal spore in the ambient air of west
Korea during the Asian dust (Yellow sand) period[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2, 36:5437-5442.
[70] 吴东辉, 胡克, 王云, 等. 长春市“2000-04-07”远源沙尘湿沉降携
带细菌研究[J]. 中国沙漠, 2003, 23(6): 652-655.
WU Donghui, HU Ke, WANG Yun, et al. Study on bacterium car-ried by remote sandsto rm “2000-04-07” with wet descending in
Changchun city, Jilin province[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03, 23(6): 652-655.
[71] CHOW J C, WATSON J G, GREEN M C, et al. Cross-border trans-port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uspended particles in Mexicali and California’s Imperial Valle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0, 34:1833-1843.
[72] ALLER J Y, KUZNETSOVA M R, JAHNS C J, et al. The sea sur-face microlayer as a source of viral and bacterial enrichment in ma-rine aerosol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801-812. [73] MAIN C E. Aerobiological, ecological, and health linkage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03, 29: 347-349.
[74] TEPTIN G M, DOURIAGUINE P N. On simulation of biological
aerosol particles distribution in turbulent atmosphere and its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996, 27: S245-246.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effect of bioaerosol: A review
QI Jianhua,GAO Huiwang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China
Abstract: Bioaerosols are a significant subgroup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and its transport should be related to spread of human, animal and plant disease epidemics. Bioaerosols have indirect effect on the altera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and atmospheric process. International bioaerosol research has been developing very rapidly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the area has received an addition-al spike of attention. Several types of biological organisms (e.g., fungi, bacteria, and algae)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effective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being active in cloud. The bioaerosols have potential role in modifying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other organic compounds upon collision or contact, and hence inducing changes in the IN or CCN ability of organics in atmosphere, and implicating them in the alteration of cloud coverage and hence the global climate. Airborne microorganism also has impact on air quality, and mos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source and monitoring of indoor bioaerosols such as fungi, bacteria and allergens. The sample validi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bioaerosols measurement. Some new and applicable on-line sampl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ies, such as Raman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and Time-of-fight Mass Spectrometer, have been developed to reduce sampling error and improve living efficiency of organisms. The atmospheric bioaerosols can be transported for a long range following some routines,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kind of bioaerosol. The recent studies on environment effect, sampling, analysis,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bioaerosols are reviewed. Key words: bioaerosol; climate change; transportation
生物气溶胶研究进展
学号:14103503
常 州 大 学
科技论文写作
题 目 生物气溶胶研究进展 学 生 吴 坤 鹏 学 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 土木环境工程
二○一四年十一月
生物气溶胶研究进展
摘要:
生物气溶胶是大气气溶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气中的扩散、传播会引发人类的急慢性疾病以及动植物疾病。生物气溶胶还可以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并对大气化学和物理过程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也逐渐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关键词:
生物气溶胶 气候效应 传输
The Progress of Atmospheric Bioaerosol Research
Abstract:
Bioaerosols are a significant subgroup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and its transport should be related to spread of human, animal and plant disease epidemics. Bioaerosols have indirect effect on the altera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and atmospheric process. International bioaerosol research has been developing very rapidly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the area has received an additional spike of attention.
Key words:
bioaerosol; climate change; transportation
引言
当前,在整个国际大气科学领域的研究中,气溶胶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是当今大气化学的最前沿领域之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气溶胶科学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创造了实验探测和数值模拟的条件,气溶胶科学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正不断地向基础学科渗透,研究内容覆盖面十分广阔,涉及工农牧林、环境、气候、医学等的各个学科领域,受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的关注,目前国际气溶胶科学的主要研究趋势已经从人为源向天然源,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源逐渐发展;由总体颗粒物的研究发展到单个颗粒物的研究,由一次微米级的颗粒物向亚微米级甚至纳米级的二次颗粒物发展。
大气气溶胶是指大气与悬浮于其中的固体和液体微粒共同组成的多相体系悬浮于大气的无数固体和液体微粒中 有一些是由陆地和水生环境的生物活动产生的这些含有微生物或生物大分子等生命活性物质的微粒称之为生物气溶胶。[2]生物气溶胶种类很多,包括空气中的细菌、真菌、病毒、尘螨、花粉、孢子,动植物碎裂分解体等具有生命活性的微小粒子。这些有生命活性的物质通常都附着在大气中的非生物颗粒上,如细菌等微生物;也有一些可以单独悬浮于大气中,如粒径很大的花粉颗粒。[3]生物气溶胶粒子的粒径范围很宽,粒径可以从10-3um 变化到102um 。粒子形貌有简单的球体、圆柱体等,也有复杂的不规则形状。
[4]MatthiasMaser 等的研究显示,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数浓度相当高,通常维持
在大气数浓度的 30%左右,而且变化很大(9天内从16%变化到了50%)。而生物气溶胶的质量浓度除了与粒子数量有关外,还取决于它们的粒径 如大气中的花粉粒子虽然数量很少,但是粒径很大,所以具有较高的质量浓度。[5]与非生物气溶胶相比,生物气溶胶的质量浓度一般较小,但有些地区生物气溶胶在总体气溶胶质量浓度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例如,在热带可以占到55%~95%)。
生物气溶胶中没有固定的微生物种类。[6]它主要通过土壤尘埃、地面水、植物、动物和人员活动等方式被带入空气,以液态和固态粒子的形式存在,在适宜条件下可以直接在大气中繁殖也可以在沉降基质上繁殖。由于微生物能产生各种休眠体,故可在空气中存活相当长的时期而不致死亡,并可以借助空气介质扩散和传输,引发人类的急、慢性疾病以及动植物疾病。除了人体健康,效应外,生物气溶胶还可以作为冰核(Ice Nuclei IN )和云凝结核(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导致云滴和冰晶的形成,从而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并且对大气化学和大气物理过程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因此,研究生物气溶胶的基本性质、分布、来源、致病机理和气候效应是非常必要的。
1943年美国开始实施“气溶胶感染”计划,60年代全面展开了生物气溶胶的各项研究 70年代其研究从军事领域扩展和深化到了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畜牧业和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7]近年来,由于公众对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关注,生物气溶胶领域的研究增加很快,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国关于生物气溶胶的研究工作开展于80年代,主要集中于空气中微生物种类、数量的调
查,但是目前对生物气溶胶性质、环境效应、分布和传输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在生物气溶胶环境效应、采样技术、监测分析、分布和传输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2、生物气溶胶的概述
有生命的气溶胶粒子(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粒子) 和活性粒子(花粉、孢子等) 以及由有生命活性的机体所释放到空气中的各种质粒被统称为生物气溶胶。[8-10]由于空气微生物是大气生物气溶胶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生物气溶胶有时又被称为微生物气溶胶,依其种类可划分为细菌气溶胶、真菌气溶胶、病毒气溶胶等。具有较大意义的生物气溶胶的粒径范围是0.1~20.0um 。生物气溶胶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涉及很多领域,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而其浓度及粒径的变异范围也较大。[11]由于空气中缺少微生物直接可利用的养料,不能繁殖生长,因此空气中无固有的微生物群系,其均由暂时悬浮于空气中的尘埃携带着的微生物所构成,所以大气生物气溶胶主要来源于土壤、灰尘、江河湖海、动物、植物及人类本身。同时它也借助大气的各种运动进行输送,有些花粉、孢子、真菌、细菌芽孢和某些立克支氏体、病毒都可由大气输送很远的距离,大气微生物的含量是其输入和衰减动态平衡的结果。国际惯用的有关大气中微生物的含量公式是:
空气微生物的含量=微生物输入量一微生物输出量一微生物衰亡量
由于大气中微生物的输入量和总衰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未有较好的数值模式能计算出大气微生物的准确浓度[12]。仅仅对影响微生物气溶胶衰减的因素进行了一些研究。
2.1、 生物气溶胶的环境效应
2.1.1、 气候效应
大气气溶胶粒子可以吸收、散射太阳辐射和地面长波辐射,影响地——气辐射平衡,从而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对云的成核作用会影响云的光学特性、云量以及云的寿命,由此对全球气候产生间接影响。研究揭示生物气溶胶可以作为冰核和云凝结核,并可以改变其它CCN (如有机气溶胶)的特性而影响云量,进而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13]此外,生物气溶胶还在大气化学和物理过程中存在潜在的重要作用:
1)通过微生物降解影响化学过程;
2)通过与大气有机物(OC )碰撞接触改变OC 学组成,从而诱发OC 作为IN 或CCN 的性能改变;
3)促进环境界面化学(包括光化学)如空气/雪界面。
2.1.2、成为冰核和云凝结核
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冰核中识别出了生物气溶胶,随后的研究也鉴别出一些细菌类生物气溶胶可以作为有效冰核,甚至在6 km的高度还发现了特定的活
第2页
性冰核细菌,它们在接近0 时是活性的(如TIN 假单胞菌属细菌 =-2 )尽管与大气中
的其他气溶胶相比,生物气溶胶的质量较小,但是它们的密度( ~103-104个/m3)和冰核的数量级大致相同,说明生物气溶胶具有作为有效冰核的潜在重要性。 生物气溶胶中的几类生物体(如真菌、细菌和藻类)以及它们的残体都被鉴别出是有效的CCN ,而且在云中以活性CCN 的形式存在。[14-15]在水汽过饱和度为0.07%~0.11%时,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 (Micrococcus agilis, Mycoplana bullata, Brevundimonas diminuta) 以活化CCN 存在,细菌细胞外表面的化学组成、结构和亲水性对CCN 活性起着重要作用。
2.1.3、对其它类型CCN 特性的影响
生物气溶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们自身可以作为CCN 和IN ,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它CCN (如有机气溶胶)特性的重要作用。一旦具有不同粒径和密度的粒子的有机化学组成发生改变,它们的CCN 特性也会受损。 大气中的有机气溶胶是形成云凝结核和冰核的一类重要物质,也是全球CCN 预算中重要的一部分。二羧酸(DCA ) 是有机气溶胶中的一类主要物质,大气生物边界层中的DCA 可以被细菌和真菌转化目前已经在7种不同的DCA 化学转变中观察到了大气真菌的存在。[16]化学转化产物中,一些是无毒或低毒性的化合物,如乙酰胺、乙酸、丁酸和丙酸,还有一些是高毒性或致癌物质(如曲菌酸)。同时还检测出了挥发性化合物如多环芳烃或杂环化合物,这表明新沉降的DCA 通过微生物过程可被循环返回大气中。DCA 并不是能被空气微生物降解的唯一一类物质,生物气溶胶还可以转化其他大气可测有机官能团,真菌可以引发大气中活性OC 的微生物降解,不同的真菌具有不同的降解速率。有机物的降解寿命变化很大,依赖于所给定的微生物以及试验因子如pH 和温度。研究还发现在有机溶液中空气微生物的存在可以改变OC 的组成[17]。这说明除了微生物降解外,生物气溶胶在与有机物碰撞接触时可以通过细胞溶解和解吸过程改变大气中有机物的化学组成以及非生物OC 的CCN 特性。因此,生物气溶胶,特别是细菌和真菌在大气OC 化学转变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目前有关生物气溶胶对大气物理、化学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影响效应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其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的了解并不深入 有待进一步研究。
2.2、物气溶胶的采检鉴技术的发展
自1676年荷兰人列文·虎克发明了显微镜,揭开了微生物学的新天地,近2个世纪后,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第一次从空气中采到并培养出了微生物,从此开辟了空气微生物采样的新领域。早期的空气微生物检验也非常简单[18-19]。到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生物化学的创立,核酸、蛋白质结构的研究成果以及划时代意义的电子显微镜的成功发明,使得空气微生物的检验,也从形态、生理生化,进入了亚分子结构和分子生物学的高级检验鉴定阶段。到了70年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科技迅速发展,空气微生物的采检也飞速发展,成功地研制出了快速自动的高、精、尖大型检测仪器,将空气微生物的采检鉴水平推向了高峰。
3、物气溶胶的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已经开始重视空气微生物的污染问题,主要集中于:1) 空气细菌、病毒、真菌、花粉和噬菌体的检测及来源的调查和治理[20]。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微生物空气污染可使肝炎、痢疾、流感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发生率增加。2) 空气污染导致传染病的发生。3) 工程菌的污染与气溶胶试验,目前很难估计有多少工程菌污染了环境,更难预料的是这些污染的工程菌对人类及其环境起到什么作用。4) 花粉空气污染仍然受到重视,由于花粉是人体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主要致敏源,其检测和预报工作在国外一直没有间断过。
80年代末科学家们正式提出生物气溶胶(bioaerosol)的定义,在1989年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年会上,首次将生物气溶胶定义为:由具有生命活性的有机体所释放到空气中,大小范围在0.1~100um 之间的大分子和易变异的混合物。自90年代开始了有关生物气溶胶的研究,首先是生物气溶胶的有效采集问题,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能够捕获的具有活性可培养鉴别的生物气溶胶种类,仅是大气中所存在的一小部分,因此国外很多有关生物气溶胶的研究都致力于快速、有效的空气微生物捕获仪器的开发和仪器问有效性比对研究,以及微生物测试分析方法
[21-22]的探索和生物气溶胶发生仪器的研制。其中某些特定致病菌的生物气溶胶的
采集与培养也成为研究热点,目前正尝试利用ATFMS (Aerosol particle time—of —flight massspectrometer)进行生物气溶胶的在线分析。由于近年在生物气溶胶工程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科学家在2003年SARS 病毒肆虐全球期间,采用先进的生物气溶胶采样分析仪器,针对空气中SARS 病毒的捕获及其性状迅速开展研究工作,从而控制了疫情蔓延。尽管对于SARS 病毒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研究发现,利用RT —PCR 技术可检测环境大气中的SARS 病毒,此结果对于今后由于意外事件或恐怖主义等所引起的生物环境空气中有害微生物的快速有效的检澳4具有积极的意义。生物气溶胶的健康效应其毒理和致病性的研究,则一直是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及整个医学界的研究焦点之一。以上的研究内容直接关系着人类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质量,所研究的环境主要局限于医院、电子、制药、食品、化妆、发酵等相对特殊的工厂和公共场所,以有利于控制这些特殊环境的潜在有害微生物的空气传播和感染;而对环境大气中生物气溶胶的环境和气候效应的研究,尽管国外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关注,发现生物气溶胶与其他污染物的浓度和类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太阳辐射对微生物气溶胶具有较强的灭杀、降解作用,明显的降低其在大气环境中的浓度[23]。但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有关大气生物气溶胶的起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车凤翔[20]首次提出空气微生物的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问题,并在北京和天津两地进行了大气微生物的初次检测,进入90年代后在我国不少大城市都开展了大气微生物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不同城市中,不同的功能区域,由于各种环境的影响,大气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浓度也各不相同。真菌孢子的大小与人类的身体健康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粒径的真菌孢子影响人体健康的作用原理也各不相
同。在经济发达、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空气微生物的种类较多,容易传播和发生各种疾病,2003年SARS 疫情的传播也正是由这些大城市向四周呈辐射状扩散和蔓延。此间,也进行了一些环境因素对于空气微生物影响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风速和风向都会影响空气微生物的浓度7,而降雨和降雪则对空气微生物具有冲刷和净化作用,能够明显降低空气中细菌粒子浓度。以上的研究大多以空气微生物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为出发点,而鲜有明确的针对大气生物气溶胶的环境和生态效应以及气候效应进行研究。
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是单一的研究空气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及浓度的时问和空间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由于采样设备相对落后,鉴定方法简单(仅是表型鉴定) ,使得多数研究仅能鉴定到属,目前已测知的空气微生物仅是大气中实际存在的少部分。
4、研究展望
虽然目前对生物气溶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认识,但生物气溶胶的来源有时难以识别, 主要是由于其来源多而分散并且难以鉴别,另外还受到气象条件的明显影响。生物气溶胶的性质研究主要集中于颗粒所含微生物的调查,但对其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尚不深入,对化学成分如何影响其CCN 或IN 特性以及化学转化的动力学和机理并不了解[24]。可见,对生物气溶胶的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其来源、转化、传输、流行疾病传播机理和气候效应作用机理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下述问题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1)生物气溶胶对大气过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作为有机气溶胶中独特的一类,生物气溶胶对大气物理、化学过程、全球气候变化存在着潜在的重要影响,但目前对其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尚不清楚。
2)生物气溶胶与人类和植物流行疾病的关系。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扩散、传播会引起人类急性和慢性疾病以及动植物疾病的流行传播。2003年 3 月全球受到非典型性肺炎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 ndrom SARS)的威胁,可是对SARS 是否借助空气传播(飞沫核和气溶胶粒子)存在很大争议[25],一方面是人们对这种新发疾病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缺乏对生物气溶胶与疾病流行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造成的。
3)生物气溶胶的源、汇及转化。生物气溶胶种类丰富、来源复杂,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进行长距离传输并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相应的转化,但目前对不同类别生物气溶胶的源 汇和转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深入。
4)生物气溶胶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及评价因子。[26]目前有关生物气溶胶的允许暴露水平的相关规定非常缺乏。为了更全面、系统地评价空气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研究生物气溶胶对大气质量的影响以及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5)生物气溶胶的时空分布规律。已有的研究揭示不同类型的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具有不同的浓度和时空分布模式,目前对生物气溶胶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但是其全球分布信息非常缺乏。
6)生物气溶胶输运、沉降过程控制机理。生物气溶胶可以长距离传输,并会将外来侵入微生物带入沉降地区,对本地生态系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但是目前对生物气溶胶的输运、沉降过程控制机理缺乏了解。[27]
7)人类活动对生物气溶胶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当前随着各种生物杀虫剂、城市污水微生物处理等微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人为因素造成的进入空气中微生物成分、数量逐渐增多。这些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生物气溶胶的形成,又会如何影响其在大气中的演变。
参考文献:
[1] 王明星,大气化学[M].2 版.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9:166.WANG M X. Atmospheric chemistry[M].2nd ed.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1999: 166.
[2] 胡家骏,周群英,环境工程微生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128-131. HU J J, ZHOU Q Y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biology[M].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8: 128-131.
[3] 章澄昌,周文贤,大气气溶胶教程[M].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5: 12.ZHANG C C, ZHOU W X. Course of Study Atmospheric Aerosol[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1995.
[4] WHITEC C, KENNYC M, JENNINGSS G . A study of marine and continental bioaerosol in the west of Ireland[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1999, 30: S809-810.
[5] ARTAXOP, MAENHAUTW, STORMSH, et al. Aerosol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for the Amazon Basinduring the wet season[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90, 95(D10):16971-16985.
[6] ARTAXOP, STORMSH, BRUYNSEELSF, et al. Composition and sources of aerosols from the Amazon basin[J].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88, 93(D2):1605-1615.
[7] HOJ, DUNCANS. Estimating aerosol hazards from an anthrax letter[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2005, 36:701-719.
[8] LEEN, HUI D, WUA, et al A major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Hong Kong[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3, 348: 1986-1994.
[9] 陈皓文, 洪旭光. 中国南极长城站室内空气微生物状况[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2000, 6(1): 90-92.CHEN Haowen, HONG Xuguang. Situation on indoor airbornemicrobes of Chinese great wall station, Antarctica[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Biology , 2000, 6(1): 90-92.
[10] 陈皓文. 吐鲁番市空气微生物浓度状况[J]. 干旱环境监测, 2003, 17(4): 211-214.CHEN Haowen. The Status of concentration of air microorganism in Tulupan City[J]. Ari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2003, 17(4):211-214.
[11] 巨天珍, 索安宁, 田玉军等. 兰州市空气微生物分析[J]. 工业安全与环保, 2003, 29(3): 17-19.JUTianzhen, SUOAnning, TIANYujun, et al. Analysis on aerobiologia in Lanzhou[J]. Industri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3, 29(3): 17-19.
[12] 张晟, 郑坚, 付用川等. 重庆市城区空气微生物污染及评价[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2, 19(3): 231-233.ZHANG Sheng, ZHENG Jian, FU Yongchuan, et al. Air pollution by microorganism 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nd its evaluation[J]. J Environ Health, 2002, 19(3): 231-233.
[13] HUDSON J G.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J]. 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y,
常州大学研究生论文
1992, 32: 596-607.
[14] LOHMANN U, LESINS G . Stronger constraints on the anthropogenic indirect aerosol effect[J]. Science, 2002, 298:1012-1016.
[15] SUN J M, ARIYA P A. Atmospheric organic and bio-aerosols as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A review[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6, 40: 795-820.
[16] ARIYA1 PA, AMYOT M. New Directions: The role of bioaerosols in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 1231-1232
[17] MAKI L R, GALYAN E L, CHANG-C M,et al. Ice nucleation induced by Pseudomonas syringae[J]. Applied Microbiology, 1974, 28: 456-459.
[18] V ALI G , CHRISTENSEN M, FRESH R W, et al. Biogenic ice nuclei, Part: Bacterial sources[J].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1976, 33: 1565-1570.
[19] LINDEMANN J, CONSTANTINIDOU H A, BARCHET W R, et al. Plants as sources of airborne bacteria including ice nucleation active bacteria[J]. Applie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1982, 44:1059-1063.
[20] SATTLER B, PUXBAUM H, PSENNER R. Bacterial growth in supercooled cloud droplets[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1, 28: 239-242.
[21] BAUER H, KASPER-GIEBL A, LOFUND M,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bacteria and fungal spores to the organic carbon content of cloud water, precipitation and aerosols[J]. Atmospheric Research, 2002, 64: 109-119.
[22] ROSS K E, PIKETH S J, BRUINTJES R T, et al. 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in CCN distribution and the aerosol-CCN relationship over southern Africa[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03, 108: 8481-8498.
[23] JAENICKE R. Abundance of cellular material and proteins in the atmosphere[J]. Science, 2005, 308: 73.
[24] ARIYA P A, NEPOTCHATYKH O, IGNATOV A O, et al.Microbiological degradation of atmospheric organic compounds[J].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2, 29: 34/1-34/4.
[25] ARIYA P A, AMYOT M. Bioaerosols: impact on physics andchemistry of the atmosphere[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1231-1233.
[26] KALOGERAKISN, PASCHALID, LEKADITISV , et al. Indoor air quality: bioaerosol measurements in domestic and office premises[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2005, 36: 751-761.
[27] FABIANM P, MILLERS L, REPONENT, et al. Ambient bioaerosol indices for indoor air quality assessments of flood reclamation[J].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2005, 36: 763-783.
第8页
生物气溶胶核酸检测技术分析
ol.37No.2V
16 舰船电子工程
hiElectronicEnineerinS pgg 总第272期
2017年第2期
生物气溶胶核酸检测技术分析
韩丽丽 齐秀丽 徐 莉
)(防化学院 北京 102205
*
真菌、病毒等微生物粒子构成,有时又被称为微生物气溶胶。生物气溶胶作为绝大多摘 要 生物气溶胶由一些细菌、
数生物战剂的施放形式,经常在生物恐怖袭击中扮演重要角色。论文在介绍生物气溶胶定义、来源、特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生物气溶胶核酸检测技术原理、优缺点、装备应用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针对我国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的研究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生物气溶胶;核酸检测技术;建议
:/中图分类号 X831 DOI10.3969.issn.1672730.2017.02.0059-j
AnalsisofBioloicalAerosoldetectionTechnolo yggy
LiliIXiuliLiHAN Q XU
(,)InstituteofChemicalDefenceBeiin02205 1jg
,Abstractioloicalaerosolisosedofbacteriafuniandvirusesandissometimesreferredtoasmicrobialaero B -gpg,formofmostbioloicalwarfareaentsbioaerosoloftenlasanimortantroleinthebioloicalterroristol.Asareleasins ggpypgg
,,,attacks.Thisaerbasedontheintroductiontothedefinitionsource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bioaerosolsummarizes pp,thecurrentbioloicalaerosoldetectiontechnolo.Italsomakesadeeanalsisontherincilesstrenthsandweaknes -yppgggyp ,,sestheemlomentofeuimentaswellasthecurrentresearchofeachtechnoloathomeandabroadandutforward ppyqpgy suestionsonthedetectionofbioaerosolareutforward. ggp
,,techniuesuestionsKeWordsioloicalaerosolnucleicacidtestin b qggggy ClassNumber831 X
1 引言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错综复杂,战争的非对称性和作战手段的多样性更加明显,尽管从1972年,以来已有1禁止生物武器公约》62个国家签署了《但是不少国家仍在致力于生物武器的研制,造成了一定的生物威胁。2美国炭疽粉末邮件001年的“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标志着生物恐怖袭击己经成为现实威胁。生物气溶胶作为绝大多数生物战剂的施放形式,经常在生物恐怖袭击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对生物气溶胶实施快速、准确的检测,已经成为防生物战和反生物恐怖袭击的重要课题。对此,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的研究,以最大限度地杜绝生物恐怖袭击
*
的发生。
2 生物气溶胶概述
2.1 生物气溶胶的定义
具有生命的气溶胶粒子(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粒子)和活性粒子(花粉、孢子等)以及由有生命活性的机体所释放到空气中的各种质粒被统称为生物气溶胶。由于空气微生物是大气生物气溶胶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生物气溶胶有时又被称为微生物气溶胶,依其种类可划分为细菌气溶胶、真菌气溶胶、病毒气溶胶等。
2 生物气溶胶的来源2.
由于空气中缺少微生物直接可利用的养料,不能繁殖生长,因此空气中无固有的微生物群系,其
修回日期:收稿日期:2016年8月3日,2016年9月17日
作者简介:韩丽丽,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生物防护与安全。齐秀丽,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生物防护与安全。徐莉,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生物防护与安全。
017年第2期2舰船电子工程
17
均由暂时悬浮于空气中的尘埃携带着的微生物所构成,所以大气生物气溶胶主要来源于土壤、灰尘、江河湖海、动物、植物及人类本身。具有较大意义的生物气溶胶的粒径范围是0.1m~20.0m。生μμ物气溶胶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涉及很多领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较为密切。
3 生物气溶胶的特点2.
体积小且无色无味,从而使得以此为施放形式的生物战剂隐蔽性较强;易渗透,使其对应的生物战剂难于防护,尤其是难于进行物理防护;易扩散,直接喷洒的生物气溶胶可随风飘到较远地区,杀伤范围可达数百至数千平方公里。
方法对PiCR技术检测结果的影响。Souchi人为地-把炭疽直接加入到空气微生物采样液中,然后用结果1个炭疽细胞在1小时CR技术进行了分析,P
内就可检出。Yadav应用PCR技术直接检测工作环境中导致职业病的分枝杆菌和假单孢菌的气溶胶总数,用于对气溶胶暴露的危险评估。ZenCR技g用P术检测了农场环境空气中walleniasebi并与培养计数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PCR技术比培养计数法更灵敏,可以检测出更小浓度的气溶胶。由于生物气溶胶沉降在物体表面可再次形成气溶胶造成二次污染,uttner研究了生物气溶胶的二次污染对PCR技B术的影响以及利用PCR技术检测物体表面消毒前后污染菌的数量以评价消毒措施是否有效。快速、灵敏度高并可对初CR技术具有特异、P
始生物气溶胶浓度进行定量分析,在生物气溶胶的检测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如今,如荧光定量CR技术及其改进技术(P多重P已广泛应用于致病微CR技术、CR技术等)P
生物的检测与鉴定领域。随着自动化与集成化程度的提高,基于PCR技术的生物战剂检测装备已开始应用于战场。例如,dah公司研制的耐用型病I原菌检测装备能够在3肉毒0min内实现对炭疽菌、梭菌、布鲁菌属、沙门菌属和李斯特菌属等的检测,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的军队配备了该装备。3 基因芯片技术3.
基因芯片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核酸探针捕获靶基因来识别生物体的种类。它通过平面微加工技术将大量的核酸探针有规律地排列固定于硅片或玻片等固相支持物上,构成二维探针阵列,用于捕获预先经过荧光物质或核素标记的靶基因,再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等技术对杂交信号进行实时、灵敏、准确的检测与分析。该技术结合了微电子、微机械、化学合成、光学、计算机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前沿技术,利用构建的基因芯片及其表面微流分析系统,快速、准确地完成对微生物的鉴定。C005年,Zhou等根据GenBank中SARSoV基2-因组序列,设计了靶向SCARSoV保守序列的寡-核苷酸探针,并将这些探针整合到70-mer基因芯片上,实现了对SCARSoV的早期检测。通过对-临床样品的检测结果表明,基于基因芯片的有效,对SCARSoV早期检测方法特异、ARS患S-
者的检测敏感性约为91%。2009年,Felder等建立了基于基因芯片技术检测环境样品中炭疽菌的方法,其构建的基因芯片包含靶向炭疽菌质粒毒力基因r蜡样芽孢杆菌
和B以及各亚型炭疽菌、op
3 核酸检测技术
微生物基因组内均含有特异的、有别于其他种或属的核酸序列,这些特征序列相当于微生物的。利用核酸检测技术检测微“身份证”或者“指纹”生物样品中的特征序列及丰度即可实现微生物的鉴别从而进一步检测生物气溶胶。
1 核酸杂交技术3.
核酸杂交技术依据碱基互补配对原理,将带有标志物的核酸探针与被检样品中的目标核酸序列特异性地结合,然后利用特定手段测定标志物,通过确定样品中目标核酸序列的丰度来实现对微生物的鉴别。如果以某种微生物的特征序列为探针,那么通过杂交技术就可以检测样品中是否含有该微生物。核酸杂交技术具有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优点,能在几分钟至几小时内检测出pg水平的基利用荧光原位杂交还可以实现目标序因组DNA;列的定位与可视化。
如今,核酸杂交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致病微生物中,以生物气溶胶形式施放的病毒、细菌、立克次体等多种生物战剂都可以被成功检测出来。2 PCR技术3.
是一种能在体外快速扩增聚合酶链反应(CR)P特定基因片段的方法,即通过高温变性、低温退火、适温延伸三个步骤,对寡核苷酸引物所界定的基因片段进行扩增,通过检测出来的DNA和RNA来实现对微生物的鉴别。Hlauand第一次用PCR技术-g检测了人工发生真菌Stachbotrchartarum的气溶yy 胶,检测值与直接镜检和已知浓度值相符,证明PCR可以快速定量空气中某种生物气溶胶的浓度。随后他又研究了真菌孢子不同DNA提取方法对PCR技术结果的影响。Ceruzrez研究了应用PCR技术检-p测环境真菌的引物和探针,并评价了各种DNA纯化
81
韩丽丽等:生物气溶胶核酸检测技术分析总第272期
枯草芽孢杆菌1并利6SrDNA的寡核苷酸探针,用该芯片对158份环境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将炭疽菌与其他杆菌有效区分,整个检测过程仅需12小时。
目前基因芯片已在生物战剂气溶胶检测领域广泛应用。多国权威媒体和刊物中都已有采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大肠埃希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鼠疫杆菌、西部马脑炎病毒、出血热病毒等和采用免疫芯片技术检测葡萄球菌肠毒素的研究报道。
但是基因芯片的制作成本还很高,并且需要昂贵的检测仪器,因此该技术主要局限于实验室研究而未能广泛应用于临床致病微生物的检测与鉴定。4 核酸检测技术特点分析3.
核酸检测技术具有如下优点:和免疫学技术优点相同,该技术具有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优点,能在几分钟至几小时内检测出pNA。g水平的基因组D
可是核酸检测技术也有自身的缺陷:该技术本身的专业要求较高,导致形成装备的难度偏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技术的应用。
5 国内外研究现状3.
西方发达国家便已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明了以PCR技术为代表的核酸检测技术。在随核酸检测技术以其高特异性、后的2高灵0多年里,敏度的优点得到广泛关注和良好发展。
汪晓辉等于1996年利用逆转录半套式PCR技术对风疹病毒气溶胶进行检测。但随后,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迟迟未能有创新进展,与西方发达
检测技术遥测免疫学核酸质谱生物发光
分析时间较快一般很快很快较快
灵敏性一般一般很强较强一般
国家的水平差距较大。
4 对我国研究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
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国内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研究较浅、技术较为落后的问题。为提高我国生物气溶胶检测水平,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本文针对我国实际研究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对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的研究力度4.
我国对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人力物力投入方面明显不够,导致一些关键技术较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而随着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向自动化、实时化、远程化的趋势发展,其在技术上的要求必定越来越高,这更是需要我国加大对此的研究力度,紧紧追踪国外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的发展动态和前沿水平,将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制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以期在不久的将来研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军特色的生物气溶胶检测技术。
2 重点发展核酸检测技术4.
检测生物气溶胶的技术很多,遥测技术、免疫学技术、核酸技术、质谱技术、生物发光技术等。每种技术各有优缺点,从目前检测技术发展的现状来看,核酸检测技术在分析时间、灵敏性、可靠性、特异性等方面均优于其他技术,结果如表1所示。
可靠性一般一般强较强差
特异性一般较强强一般差
设备一般复杂较复杂一般简单
备注商品化商品化发展中商品化商品化
表1 各种检测技术的比较
但是其 虽然核酸检测技术有以上多方面的优势,
对专业技术的要求较高,一些关键技术尚未得到优化,仍需广大科研人员继续攻坚克难。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核酸检测技术上,做到优化技术,简化流程,高效地完成对生物气溶胶的检测。3 尝试发展集多种检测技术优点于一身的新型4.
技术
生物气溶胶的检测已经发展为一个涉及多种学科与技术的系统工程,它包括遥测、免疫、核酸、质谱等多种技术。每种技术都含有其特定的优缺点,经研究发现,有时仅靠一种技术很难高效地完
成对生物气溶胶的检测。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先进国家已开始研究由几种技术、几种仪器组成的JBPDS系统来解决某些复杂的生物气溶胶检测难题。我国应跟随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尝试发展集多种检测技术优点于一身的新型技术,以期高效的完成对生物气溶胶的检测。
参考文献
[]许强,金伟其,董立泉.超光谱侦察系统的光学参数设1
]():计[北京理工大学学报,9J.2006,261089806.-
(下转第24页
)
42
李 宁等:海上作战指挥训练评估方法研究
参考文献
总第272期
。果为“良”
6 结语
本文突破海上作战指挥训练评估对象以受训者,即海上作战指挥机构为主的传统做法,将训练内容设计、训练计划拟制、训练实施保障等训练组织环节,以及指挥训练环境和条件模拟、作战效果裁判、系统稳定性和恢复能力等,指挥信息系统训练功能的效能也纳入到海上作战指挥训练评估对象范畴。按照此思路,构建了基于组训、受训和指挥信息系统三要素的海上作战指挥训练评估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模型,提高了海上作战指挥训练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评估模型求解主要采用基于灰色理论的层次分析法,通过将专家的定性评判转化为灰类程度不同的评估指标权重向量,再经过对该向量的一致性检验和归一化处理,形成定量的评估判断,实现评估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一方面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评估模型的计算准确度。通过实例验证,该评估模型及其求解方法对于提高海上作战指挥训练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效果良好。
[]戴钧陶.现在管理评估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1M].
社,994:659.61-
[]张卓.作战系统效能评估[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M].
996:871.19-
[]毕长剑,董冬梅.作战模拟训练效能评估[北京:国3M].
防工业出版社,014:474.25-
[]张海波,胡剑光,常国任.基于模糊评价的水面舰艇综4
]():合性能评估[舰船电子工程,007311114.J.21-[]刘宪,王平.基于灰色层次分析法的舰载机部队训练评5
]():估[舰船电子工程,J.22016358.2-
[]郭齐胜.装备效能评估概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6M].
社,21005:10006.-
[]黄希利,杜红梅,罗小明.通信对抗系统作战能力评估7
():]模型[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0102836.J.28-[]张笑,徐廷学,范树海.基于灰色层次分析法的武器系8
]统综合保障能力评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学报,J.():23009335155.-
[]黄勇,孙德翔,邢国平.基于灰色层次分析法的装备备9
]():件重要度评价[航空维修与工程,J.2010468.66-[]邵帅,戴明强,张肖.基于正态云关联度的军事后勤仓10
()]:库选址评估[兵器装备工程学报,0162658.J.26-[]覃菊莹.南宁:广西大灰色层次分析法-GAHP[11D].
学,2002:5.52-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静雨.美国抗击生物恐怖战的医学技术开发与进展(11上接第18页)
[]陈峰,吴太虎,王运斗.生物及化学毒剂侦检技术发展2
]():现状[医疗卫生装备,J.27011,32.7-
[]罗振坤,王秋华.化学/生物战剂激光雷达探测技术3
()[]:医疗卫生装备,J.2011,321814.8-
[]曹秋生.]化学/生物战剂探测与激光雷达[电光系4J.
统,011,3:128.-
[]高树田,张晓峰.现代生物战剂检测技术及典型装备5
():[]医疗卫生装备,010,31313.J.255-
[]云云,]汪长中,吴璇.病原微生物检测技术进展[安6J.
():徽医药,2013,17350103.5-
[]连英姿,董雪,李勇.7ATP生物发光技术快速检测水中
]:细菌的研究[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J.007,17(10)859860.11-
[]李伟,王静,胡孔新,等.应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建立8
]炭疽杆菌芽孢的快速检测方法[中国国境卫生检疫J.():杂志,2004,27632931.3-
[]蒋韬,梁仲,陈涓,等.口蹄疫病毒O,A.A9sia1型定型
]诊断胶体金免疫层析方法的建立[中国农业科学,J.():23008,4111801808.3-
[]章澄昌,周文贤,人气气溶胶教程[北京:气象出版10M].
社,1995:32841.3-
[]():国外医学情报,J.22002,2311289.-
[]徐毓龙.]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传感器[电子世界,12J.
():,27002,178981.-
[]杨瑞馥,韩延平,宋亚军,等.炭疽芽孢杆菌检测鉴定13
](:技术研究进展[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002,302)J.25536.-
[]马立人,刘志红.反恐怖活动及生物和化学战剂的检14
]():测[现代科学仪器2J.20121194.-
[]朱元,郑海洋,顾学军,等.大气气溶胶的检测方法研15
]():环境科学与技术2究[J.005,628175.
[]黄烨,方勇华,熊伟,等.污染气体红外光谱仿真及参16
]():数设置研究[光电工程,J.2006,336614.6-[][]17FlannianB.irforFuniinindoorenvironmentsJ. gg
,():J.AerosolSci.1997,28338187.3 -
[]K18siazekTG,WestCP,RollinPE,etal.ELISAfor
[]thedetectionofantibodiestoE,bolavirusesJ.Jln -,():ectDis1999,179119298.f1 -
[]W,19anJYanY,ZhouL,etal.Simultaneousdetec -gg
ionoffivebiothreataentsinowdersamlesbat gppy multilexedsusensionarraJ].Immunoharmacol ppy[p,():lmmunotxicol2009,31341727
.o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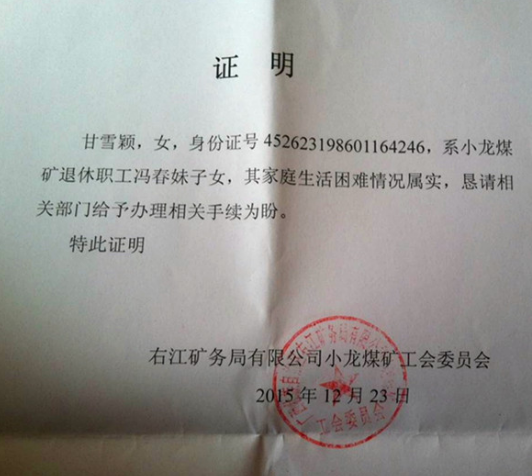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丿灬岩
丿灬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