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一:贾宝玉为什么爱读《西厢记》?
王溢嘉
【人性探微】贾宝玉为什么爱读《西厢记》?
因为严厉禁止,使原本平凡的东西产生了特殊吸引力。
贾宝玉原来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但在《红楼梦》第23回,他在书坊发现许多古今小说和传奇角本,立刻如获珍宝,悉数买回。
一天早上,正在桃花底下津津有味地读著《会真记》(即《西厢记》)时,黛玉刚好过来,问他看什么书,宝玉慌得藏之不迭,推说是《中庸》、《大学》。黛玉不信,宝玉只好将书摊开来,说:“好歹别告诉人去。……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於是黛玉也接书来看,而且越看越爱不释手。
宝玉和黛玉的沉迷於《西厢记》,除了宝玉说的那“真真是好文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西厢记》在当时乃是一本禁书,所以宝玉才要遮遮掩掩。这就是所谓的“禁果效应”,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会越让人注意,也越具有吸引力。“禁果”指的是伊甸园里的苹果
,亚当为什么会渴望吃苹果呢?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被上帝禁止的如果是那条蛇,那么亚当想吃的可能就是蛇。”真正诱人的并不是苹果或《西厢记》,而是“被禁止”这三个字。如果《中庸》、《大学》被列为禁书,那么贾宝玉渴望读的可能就是《中庸》、《大学》而不是《西厢记》。
心理学家弗利曼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小学生在玩具屋中玩各种玩具,其中有一部电动机器人。在玩了一阵后,老师对某一组学生发出“不准再玩电动机器人”的禁令,结果该组学生都改玩别的东西,不敢再玩那部电动机器人。改天,另一位老师又带同一群小学生到该玩具屋玩耍,结果,原先被禁止玩机器人的那组小学生变得特别喜欢去玩那部电动机器人,觉得它更有吸引力。这种特殊的人性,显然在儿童期就开始浮现。任何东西只要加上个“禁”字,譬如禁果、禁书、禁药,就会让人觉得更神秘、更刺激,而千方百计想去弄个来试试、玩玩。除了你越禁止我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的心理反动因素外,还有一个诱因是触犯禁令所获得的快乐,乃是双重的快乐。
上帝禁止亚当吃苹果,老师禁止学生读禁书,父母禁止青少年谈恋爱,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你除了摇头叹息外,更应该了解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你的“栽培”——因为你的严厉禁止,使得原本没有什么的东西“物超所值”,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你不能怪孩子“少不更事”,应该怪自己“老不更事”。
范文二:西厢记中红娘有什么作用
《西厢记》中红娘有什么作用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表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美好愿望的著名故事之一,崔莺莺和张生曲折而真挚的爱情佳话广为人们熟知。而在文中,促成崔张二人的爱情转化为婚姻,有一个人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就是莺莺的侍女——红娘。
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这样评道:“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足见红娘的作用是多么重要。下面,就来具体分析红娘都有哪些作用。
首先,红娘作为崔莺莺的侍女,就像一条线索,将各个人物相互串联起来,是他们互动的桥梁,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在剧中,红娘是老夫人派去服侍代“撒沁”的,因而崔莺莺把她当做老夫人来监视自己的“眼线”而有所防备;同时莺莺的一举一动、细微的心理变化,又都可以通过侍女这一亲密而独特的视角而展现出来。如莺莺与红娘在后花园烧香,第一柱、第二柱香分祝父母,而第三柱香却沉吟不语,虽然莺莺不便在红娘面前直言,但红娘已觑破了莺莺的心思,“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将小姐的心思通过红娘的口说了出来。对于张生来说,红娘更是起着重要作用,第二本第三折,红娘去请张生,红娘的旁白恰如其分地将张生的心绪给抖露出来,“一句‘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报前,‘姐姐’口乎之,喏喏连声。”将张生的急切展露无余。对郑恒来说,他想接近莺莺打听消息找红娘无遗是合适的人选,同样借红娘之口表明郑恒的品性:“郑恒是小人浊民”、“倚父兄仗势欺人”。红娘像是一个连接各个结点的网,老夫人因报答张生,使红娘有了张生与莺莺直接接触的桥梁;莺莺与张生之间“一波三折”的真挚感情直接影响了红娘,从而也引导着红娘从中周旋促进他们感情的发展,红娘维系了各人物间关系松紧的变化。
起初红娘对张生并无好感,认为张生“世上有这等傻角!”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后,她对张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为张生救了一家的性命而敬佩,感激他。这时她对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也有了充分的了解。莺莺与张生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相当般配。于是在封建礼教盛行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红娘挺身而出,穿针引线,往来调停。在第一本四折“闹斋”一场戏中,崔张二人眉目传情,爱情已在心中萌生,红娘“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催开了在封建礼教、家族秩序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相思之花。红娘同情莺莺的处境,她觉察到崔张情意后,有心成其好事,“听琴”一折中,红娘陪伴莺莺到后花园,通过咳嗽告知张生,当莺莺沉浸在琴声中时,红娘便借口离开花园,临走时,她还高声对莺莺打了个招呼“姐姐你这里听,我瞧夫人一会便来”。既为崔张二人留下了独处空间,也防着夫人,以免被发现,可见红娘十分聪明与细心。后当张生绝望,害相思病,茶不思饭不想时,红娘站出来劝他去
应考,考取功名改变老夫人的看法;当张生去京应考,郑恒从中插足,对于郑恒的无理霸道,红娘又站出来不卑不亢痛骂郑恒。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红娘正是崔张二人的红线,少之 ,则是珠玉散落。红娘的每一次出场都非常及时,挽回局面,在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协调着各方,推动着剧情的转折。
再次,红娘作为一个侍女,似乎独立于崔莺莺、张生、老夫人、郑恒的关系之外,可以用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主人公的故事的发展,正与读者的阅读视角相符合。所以,作者可以借红娘之口,来透露自己的观点,与读者进行交流,表达出自己想要告诉读者的内容。红娘虽聪明伶俐,但她的许多议论显然已超出侍女的身份,表现出一定的超越性。红娘虽然同情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但也勇于揭露和反抗莺莺的“假意耳”和“乖性儿”,对张生种种缺点进行调侃和嘲讽;对于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封建主义代表人物老夫人和郑恒也不畏缩退让。在“拷红”一折中,红娘没有被“刑讯逼供”吓倒,沉着冷静、机智灵活的与老夫人辩解,最终转守为攻、扭转乾坤。面对郑恒的恐吓“姑娘若不肯,著二三十个伴侣,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个婆娘!”红娘则敢于顶撞,义正辞言。红娘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使她虽是一个配角,却在剧中是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存在。
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如此看来,也是言辞中肯,若是没有红娘这一催化剂,恐怕崔莺莺与张生最终也难成眷属。
范文三:《西厢记》究竟是“妙词”还是“淫词”
《西厢记》究竟是“妙词”还是“淫词”
2012年02月20日09:41 东方早报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的性描写主要仍是用传统的写意手法,比《金瓶梅》的写实手法要含蓄得多,抽象得多。这恐怕就是《西厢记》原本不仅从未出现过删节本、洁本,而且始终在舞台上演出的原因。
蒋星煜
《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
翁敏华著
学林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369页,28.00元
《西厢记》问世以来,历来评论家均给予好评,也有一批以卫道者自居的,如明代何良俊之流,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淫词。最别出心裁的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对《西厢记》用了非常形象化的手法,十分聪明地把当时大观园中各色人等对《西厢记》的内心深处的热爱、表面上的一意贬低像工笔画般精雕细刻了一番。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标题为《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不言而喻,曹雪芹认为《西厢记》用心描摹崔莺莺与张君瑞的爱情故事的语词为妙词,并非淫靡之语也。
曹雪芹的时代是清代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年之久。就中国而言,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改革开放,社会有了飞跃的发展,应该说封建观念基本上清理得差不多了,尤其对于爱情、对于性文化,也许转变得太快,失去了分寸的也有。而翁敏华教授关于《西厢记》的述评,却让我大吃一惊。
其《性崇拜及其在戏剧中的面影》一文(原载《中国戏剧与民俗》,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年),将结束时说:
东方传统戏剧的台本中,每每有大量的艳言猥语,令今人不堪入目。《西厢记》的唱词宾白就十分淫靡。尤其张生,大量的“下流话”使他几乎不符合身份。莺莺的唱词也很露骨。
我不知道翁敏华对《西厢记》是否真的如此评价,但使我不禁想起曹雪芹巧夺天工的处理。当贾宝玉先把《西厢记》给林黛玉看了,后来又对她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以后,林黛玉立刻满面通红,“薄面含嗔”,叱责宝玉:“……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也许会有人以此为依据,断定林黛玉锁定《西厢记》为“淫词”的。
其实,前面还有一段文字: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这才是她对《西厢记》的真实看法,之所以说成“淫词艳曲”,还声称要向贾政、王夫人告发这件事,原是逗弄贾宝玉,说着玩的。或者说,在大观园中,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公开表示对《西厢记》的热爱是不合时宜的。
林黛玉虽然不可能在大观园中谈论《西厢记》的文词,但她也没有设法隐瞒自己读过《西厢记》,《红楼梦》的第四十四回,凤姐要鸳鸯行酒令时,当然黛玉也得说一句。她们是这样说的:
鸳鸯:左边一个“天”。
黛玉:良辰美景奈何天。
鸳鸯:中间“锦屏”颜色俏。
黛玉:纱窗也没红娘报。
按黛玉对诗文的熟悉程度,她完全可以说任何别的东西,她却偏偏第一句说了《牡丹亭》,第二句说了《西厢记》,这是她的性格决定了的,无法改变也。甚至第五十一回中,宝琴吟诗《蒲东寺怀古》,要宝钗表态时,她也装着对《西厢记》一无所知,只推说“却无考”,企图搪塞过去。仍旧被黛玉加以点破,使之十分狼狈。当然黛玉是曹雪芹所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这一些情节都说明曹雪芹对《西厢记》评价之高,在论争时,寸步不让。
历代戏曲理论家对《西厢记》的评价如何?现择要列举之:
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称此剧“天下夺魁”,也就是说,如果把元杂剧制作排行榜,其榜首即《西厢记》,这是总的评价,也包括流行之广在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唱词、宾白“天下夺魁”,但整个剧本就是唱词、宾白两部分组成的。因此,钟嗣成当然是赞赏其唱词、宾白的。
到了明初,宁献王朱权乃朱元璋第十六子,当朱棣成为明成祖之后,对这个兄弟采取了严密监视的办法,他知道朱权才略过人,所以必须防范,必要时找一借口杀掉。朱权的日子过得不太平,诚惶诚恐。他著《太和正音谱》,其《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一章谓: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
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按王实甫所作杂剧种数不多,传世之完整作品仅《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西厢记》之知名度超过其他两种多矣!花间美人之誉,称赞《西厢记》自无疑问。二十世纪中叶研究《西厢记》之专家王季思有《西厢记》校注本问世,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一再重版。书中有附录:《关于西厢记作者的进一步探讨》,说:“《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称,'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这里所形容的王实甫的词曲风格跟今本《西厢记》基本符合。” ?明代中叶以后,论《西厢记》的词采的人颇多,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西厢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王骥德著《曲律》,校注了一部《西厢记》,也推崇“西厢,风之遗也”,“西厢似李”,他与胡应麟不约而同地将《西厢记》与李白的诗相提并论。 ?王骥德又将《西厢记》与封建统治阶级比较欣赏的《琵琶记》作比较,认为“《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清初李渔对《西厢记》爱之甚深,或称誉为“千金狐腋”,或称誉为“一片精金”,似乎感到言语难以形容。《闲情偶寄》之《词采第二》则说:“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把话说得毫无保留的余地了。 ?“五四”以来,当代文学艺术界学贯中西的郑振铎,对古籍的保存、收藏、传承做了一系列工作。《西厢记》是他的重点之一。他主持工程浩大的《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第一集就收进了明刻善本弘治岳刻本、刘龙田本、张深之本三种《西厢记》。都是他亲自在上海等地茹苦含辛收购到的。果真此书属于“淫靡之词”,他决不能付出各方面重大的代价而这样做的。 ?而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便有人贬低、指摘此书,而且明、清两代,版本之多无以复加,而始终没有出现过删节本、洁本,可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爱护、认同的。 ?再看国外,这两三百年以来,无论中国国内有任何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文艺思潮有过急遽的变化,对于中国古典戏曲的翻译与介绍始终以《西厢记》居英、法、德等语之首位。到了1995年,加州伯克利大学韦斯脱(West Stephen H)与哈佛大学伊维德(L Idema)两位教授合作完成了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弘治岳刻本《西厢记》全译,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令全世界所有中国古典戏曲爱好者有了欣赏《西厢记》原貌的机会,真乃大盛举。 ?在日本,他们尚采用汉文的时代,《西厢记》就广泛流行,改用平假名、片假名的日文(和文)以后,日文译本就陆续出现,而且有训译本、歌译本等不同体例的译本出现,远山荷塘、盐谷温、田中谦二等均有译本,研究《西厢记》的专家如波多野太郎、岩城秀夫等,也很多,不仅没有出现过删节本,他们在评论《西厢记》的专著中也从未认为《西厢记》是“淫靡之词”也。 ?话说回来,《西厢记》的《月下佳期》一折,确实有〔上马娇〕、〔胜葫芦〕、〔幺篇〕、〔后庭花〕四支曲子对性生活有直接的描写,尤其〔胜葫芦〕: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几乎成为卫道君子们的众矢之的,莫不认为“淫靡之词”。其实王实甫这些描写主要仍是用传统的写意手法,比《金瓶梅》的写实手法要含蓄得多,抽象得多。这恐怕就是《西厢记》原本以及传奇改编本《南西厢》的《佳期》不仅也从未出现过删节本、洁本,而且始终在舞台上演出的原因。在国外,当然更不致引起非议,因为这方面的描写,远逊于他们的经典名著《十日谈》那么具体,当然比英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露骨的直白的展示,更是望尘莫及。 ?此曲王实甫将女性性器官喻之为牡丹,应该说是不同寻常的处理,因为牡丹在唐代先成为美女的象征,又是盛唐时期繁荣昌盛的象征,实际上已成为“国花”了,所以先后被李正封、白居易等诗人誉之为“国色”、“天香”。这情况,翁敏华不可能不知道。 ?翁敏华在《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一书中,第三章为《性崇拜及其在戏剧中的面影》,先说到“探索性崇拜意识与东方戏剧的发生关系”是“本文所力图做到的”,也这样做了。并举日本早先的艺能叫“田游”,“也有举男根女阴道具表演的”。又说:“现今最常见的是由——翁——妪(皆戴面具)拥抱而舞,作交欢状。”那么,在王实甫的时代用写意的手法交代“交欢”又有何不可呢? ?我认为王实甫用牡丹象征女阴也可以认为是古代性崇拜在元代戏曲中的反映。王实甫认为张君瑞、崔莺莺的爱情纯洁真挚,《月下佳期》的幽会是灵肉一致的结合,所以才用国色天香的牡丹。任何文化都有传承发展的过程,王实甫《西厢记》的《月下佳期》正是过程中的一个标本,称为“淫词”,在分寸上显然失控了。 ?清代金圣叹在他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对《月下佳期》(金本称《酬简》)有十分干脆的看法,他说:“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看来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王实甫用的写意手法,而且写得很美。与《金瓶梅》里那些非常直白而庸俗的描写有天渊之别,所以士大夫也容忍了。人们没有因为金圣叹本不顾其戏曲结构、舞台效果任意删削而舍弃之,反而在清代最流行,版本将近百种,也许他这一番言论深得读者之心,所以就畅销了。 ?在国外,《西厢记》译本极多,到目前为止,仍以用金圣叹本者居十之七八,原因何在?大可研究。也可能和他对《月下佳期》的评论和西方的文艺工作者更接近吧! ?我们知道元代的文化与宋代文化属于不同类型。元人精通四书五经者较少,但由于游牧民族尚未多受封建礼教熏陶,因此,对于男女的爱情问题反而比较开放。王实甫敢于在《月下佳期》中如是处理,不仅是他个人的才华、热情,可能蒙古族的习俗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注意到了翁敏华认为张君瑞的某些说唱是有失身份的,他是尚书之子也。《红楼梦》中,黛玉、宝钗都是贾府至亲,身份相等,黛玉敢于和宝玉背地阅读,总的感觉是读后“余香满口”,宝钗甚至一定要假装根本不知道《西厢记》的剧本,当然也不知道故事情节,当然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为此,我曾写《〈西厢记〉——大观园中的一面镜子》把好几位小姐的虚伪的或尴尬的或机智应付的镜头都显示了一下。 ?作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又是一位女性,翁敏华在三部中国戏曲史著作中,对古代民俗中的性崇拜、性交崇拜都有精辟的论述,的确有胆有识,在研究中国戏曲史这一领域是第一人。但是她却如此评价《西厢记》,令我不解。当时张君瑞所用的语言,崔相国之女莺莺觉得很真诚可爱,愿以身相许。王实甫为之发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赞美之词。我认为风俗习惯乃至整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彼时彼刻张君瑞、崔莺莺仍举着男根女阴的模型而舞呢?恐怕更不合适罢。中外圣贤周公、孔子、柏拉图等都没有留下男女相爱达到高峰时的规范语言,咋办呢? ?张君瑞的语言也许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比《金瓶梅》中色情狂西门庆的语言已经净化多了,比较诗情画意,何“下流”之有。 ?翁敏华第三部中国戏曲史论著《古剧民俗论》写得很充实,能广泛联系日本、韩国戏剧作比较研究,对中国民俗的关注则较前辈戏曲家黄芝冈、徐嘉瑞等更多、更深入,作为女性,对剧中女性的命运演变比我们的理解也更到位。但是,她对《西厢记》的唱词似乎清规戒律过多,担心过多,批判过严,拒之过远,仍视为“淫词”。那么,“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也是“淫词”么?因为“成眷属”的男女双方虽然不可能是“性崇拜者”或“性交崇拜者”,但是既然成眷属,也就必然有“性生活”的,而且过程中也有语言交流的。咋办呢? ?我们决不能允许社会淫靡、混乱之风盛行,公安部门为之做了大量工作,是必要的。现实社会中某些《色│戒》等拥有大量观众的影视作品应如何评论,该是首要问题,且慢将“淫词”之罪状加在《西厢记》头上吧! ?再说《牡丹亭》在这方面的宾白、唱词,如《惊梦》、《寻梦》两出中的〔鲍老催〕、〔山桃红〕、〔品令〕、〔豆叶黄〕等曲对性的描写较《西厢记》更多更细腻,为什么不加批判呢? ■ ?(责任编辑:文娜)
?欢迎光临木柳书屋
范文四:西厢记的作者是谁
《西厢记》古代经典的爱情小说
《西厢记》的作者是谁?《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剧本描写书生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
《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争。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而且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展开的冲突。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
此外,《西厢记》还有由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这些冲突虽然属次要,却是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这正是《西厢记》令人叫绝之处。《西厢记》的角色不多,戏却很多,情节曲折。
《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因此它避免了其它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余地展开情节、刻划人物。这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
《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成是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王实甫很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卓越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版本数量众多,流传至今的明清刻本约有一百种。明清两代的众多学者对《西厢记》评价很高,直到近现代,《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赞赏。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范文五:《西厢记》杂剧的作者是谁?
描写崔莺莺与张珙的恋爱故事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数百年来,它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深深叩动着青年男女的心弦,连《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元刊本现在已无从见到,现存的大都是明人枝订本。也正是从明代开始,对于它的作者是谁,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元末锺嗣成的《录鬼簿》认为是王实甫,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及稍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持有同样看法。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西厢记》是关汉卿作或者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和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三种意见。《西厢记》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所谓“关作王续”、“王作关续”,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关补续。王实甫和关汉卿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厢记》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各家都拿不出证据确凿的理由来,主张“王作关续”最早的明代戏曲作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指出《西厢记》第五本“雅语、俗语、措大语、自撰语层见迭出”,文学风格和语言与前四本不统一。明末卓人月将《西厢记》第五本和前四本分别与宣扬“始乱终弃”的《莺莺传》作了比较,认为《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全失矣“(《新西厢》自序),也主张”王作关续“。明崇祯十二年张深之校正本,更是明署”大都王实甫编,关汉卿续“,到了清初,金圣叹批本《第六才子书》盛见流行,”王作关续“说也几乎就成了一时之定论了。
解放后,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都认为《西厢记》为王实甫一人所作。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所谓“王作关续”,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厢记》的排斥和丑诋。谭正壁也认为,《录鬼薄》和《太和正音谱》的说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认为,关汉卿也是作过《西厢记》的,不过不是杂剧,而可能是小令(《乐府群珠》卷四中,就有关汉卿作的总题为《崔张十六事》的《普天乐》小令十六支),这就是后人误传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记》杂剧的由来。从60年代初开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例如,陈中凡既否定王实甫独作说,也不赞成“王作关续”说。他认为,《西厢记》确实原属王实甫的创作,但那不是多本连演的杂剧。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到底,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打破了这些限制,在王实甫生活的元代前期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则,《西厢记》与公认为王实甫所创作的《丽春堂》等剧相比,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有极大的差异。
因而可以推知现存的《西厢记》是在元曲创作阵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戏影响后,由元代后期曲家改编而成的。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本遵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不尽相同,自由运用声腔尤见进步,证明第五本尤为晚出。不久前,又有人从《西厢记》全剧情节发展的时间上的疏漏,结局与主题的不同等方面,论证了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认为《西厢记》,在第四本“惊梦”之后便告结束,不仅符合我国传统戏曲的结构特点,而且改变了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来结尾的通病,否定了夫荣妻贵、衣锦荣归的封建正统观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极其高明,而第五本的结局,只有在元末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由于重新开放科举仕进之阶而有了一些变化之后才可能产生。同时,从史料记载来看,无论是最早有关《西厢记》记载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还是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只摘引了《西厢记》前四本,而没有任何第五本的资料,因此推断“王西厢”的原本应是四本,金圣叹将第五本定为“续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贾宝玉为什么爱读《西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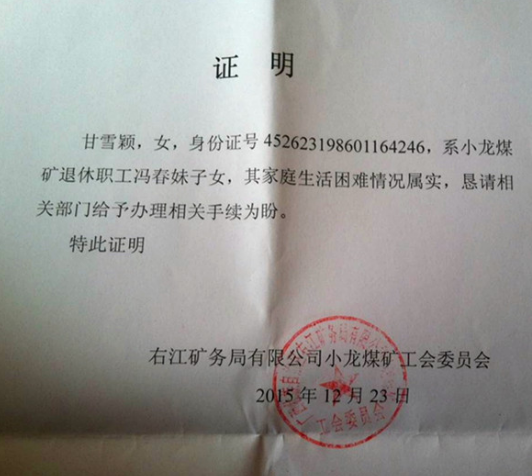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酱酱酱
-酱酱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