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一: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青年时期,我极少接触京剧。1940年冬天,我因孤岛形势日益恶化,决定离开上海去大后方。中学同学王南群、过振东为我送行,请我在卡尔登观看了周信芳的《文素臣》,周信芳、高百岁诸位的表演很精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整整九年,没有再观看过京剧。 194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那时天天看戏,也经常见到周信芳,但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1950年5月,华东文化部成立,我调到戏改处,不久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周信芳出任院长,我和周信芳打交道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1951年,中国戏曲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吕君樵、张震和我负责初试,录取了生行的钱浩梁和旦行马晨曦。复试请梅兰芳、周信芳主持,干部则仅我一人到场了。周信芳经常来衡山路十号,因为来得较早,我们就随便谈开了。后来考生唱的戏是《追韩信》,周信芳笑了,他说:“不一定要唱我的戏啊~”我向他作了解释:“事先考生根本不知道谁来对他们复试。”周信芳听了钱浩梁(浩亮)的唱,基本上表示满意,认为嗓子不太好,是青春期常有的现象,很快会好转的,于是,他又问了这个考生一些其他问题。考生退场,他表示可以录取,又对我说:“原来是钱麟童的儿子,他父亲我熟悉。”这一次复试工作,我和周信芳一起两个小时,对他的办事认真细致、对青年的爱护都有了出乎意料的体会。因为对周信芳这样的名表演艺术家来说,这确是小事一桩也。他推脱事情忙,不来,也完全可以。当然,梅兰芳也准时到达了,对于旦角的考试,也极其认真细致。 就在这一年,周信芳演剧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在上海出版的特刊上有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一篇十分简短的祝词,是陈望道部长叮嘱我拟的初稿。华东文化部及所属戏改处都送了用整幅宣纸写的祝词各一轴,都是伊兵处长布置我写的颜体楷书,字相当大。因为这些只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做的工作,当然没有告诉周信芳本人我分别是拟稿者、书写者,所以周信芳始终不知道。现在那本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特刊仍有收藏、流传,那两轴颜体楷书早在“**”中被毁了。 1953年,华东文化部改组为华东文化局,我到华东戏曲研究院做资料研究工作,和院长周信芳经常在一起谈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剧目,我们彼此发现都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七岁时以“七龄童”艺名而蜚声京剧舞台,对文史学术有这样的基础,使我完全出乎意外,也颇为钦佩。没有恒心和毅力,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在旧社会成长的一大批戏剧艺术表演家,像他周信芳,真是凤毛麟角也。 他每次来到院部,如果不是有会议要开,毫不例外地总是先到资料研究组兼作图书室那一个大厅,和大家谈,或翻阅图书。关于京剧唱、做、念、打诸问题,他基本上找徐筱汀(徐慕云之弟)谈,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上找我。很快,我们彼此都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那时候中央文化部、中国京剧院、中国戏剧出版社都忙着剧目审定工作,决定先把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的代表作予以整理出版,予以推广,也是对所有戏曲表演艺术界剧目审定工作的推动和示范。北京经常来文来电催促,不仅如此,有时还派戴不凡到上海,抓得很具体。有一天,周信芳却约我单独谈话,谈的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定稿问题,他拿出了当时的演出本,实际上也是他亲笔写下的手稿,还有一张纸,是田汉的意见,那是对三四句唱词有所修改。周信芳说:“现在都交你,请你替我拿个主意,把本子定下来。”因为这本子已经在舞台上演出多年,成为经典了,岂是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可轻举妄动的,至于田汉,他是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局长,既是权威,也极在行,因此我一再推辞,他却不肯改变他的决定。我又说:“院里编审室的京剧组也许比较适合做这件事。”他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京剧业务,他们比你熟悉,但是对《史记》、《汉书》,你比他们熟,这是历史剧,还是请你拿主意比较合适。”就这样,我真有点诚惶诚恐,把任务接下来了,大约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交还本子。究竟采用了田汉的意见没有,已记不清,但是,这对我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周信芳也没有再有任何反复,《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记》说明此剧由严朴、蒋星煜协助整理,严朴是编审室京剧组组长,所以也有他的名字,实质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他并未参与。 为了配合《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的发行和宣传,《光明日报》同时组织我写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人物描写》,在副刊《东风》发表,我也正好借此机会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此文后来被收入《周信芳艺术评论集》,于1982年12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后来曾再版过,剧本未有任何改动,但协助整理者姓名却变了。这种事情我经历多了,没有精力去交涉。 华东戏曲研究院那里先后两年多,和周信芳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主演的戏我印象颇深的除了《四进士》、《萧何月下追韩信》、《打严嵩》、《清风亭》、《坐楼杀惜》之外还有《秦香莲》,这个本子集中各剧种本子的精华,执笔者为严朴,但也可以说是周信芳亲自改编,字字句句均出于他的口述,严朴“执笔”而已,采取了包审包断的框架。周信芳一人饰两角,前为丞相王延龄,后为开封府尹包拯。王延龄为一熟悉世故人情近乎圆滑之老官僚,但还有一些正义感,可又怕担风险,性格复杂。周信芳塑造之王延龄恰到好处,与《四进士》之宋士杰异曲而同工。相形之下,包拯反而比较一般,唱腔并未向净角靠拢,但尽可能淡化了迷信色彩加深了人情味。彩排、公演、华东会演,我看了三次。我向周信芳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延龄身为丞相,他解决不了的案子,叫秦香莲去向开封府告状,于情于理似乎说不通。因为开封府尹的官固然不小,但总比不过丞相也。周信芳听了也笑了,他对我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老戏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首先如此处理的,但是,你的疑问我也早就想到了。戏这样编,不能说它荒唐离谱,多少也有一点依据,或者说有由来的。我查阅了《宋史》,原来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赵恒没有做皇帝之前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当时人们心目中,这开封府尹的职权实际上已超越了法律文本所规定的范围,而仅次于皇帝了。”我去翻阅了《宋史》,果然如此,从此对他更加钦佩。1961年,北京、上海都为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周年而展开了庆祝活动,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略谈周信芳史学修养》,2月2日发表于该报,也谈到了他关于《秦香莲》、关于包拯的谈话。
十分遗憾的是周信芳的《秦香莲》也极少有人谈起,这一版本的演出更成了绝响,能够前王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延龄、后包拯这样一人饰两角的表演艺术家恐怕也难找了。 我还和周信芳一起在台下看过金素雯、陈正薇、沈金波诸人合演的《皇帝和妓女》,他发表了感慨,他说:“像范琼这种类型的坏人,肯定现在也会有,当然不多。隐藏得很深,不容易发现罢了~”也许他有所指,我没有追问。 随着华东大区的撤销,1955年华东戏曲研究院也将不存在,同时分别成立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戏曲学校等机构。许多同志建议:出版一本纪念册。秘书长伊兵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落实了这件事情:一、院长周信芳以及院内各级领导和主要编、导、演、音乐、舞美都写点经验或心得体会;二、为了不影响机构改组、移交等工作,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作组,在上海越剧院内辟一室作为办公室。这一切都异常顺利地在进行。 这个工作组共三人,伊兵指定以我为主。我立即和周信芳院长联系,他一口答允,但他说了大意,要我成文。作为工作总结的第一篇,主要是谈对戏曲遗产的看法,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一概否定,但也应该允许作某些改动。所用的语言从现在来看,也许“左”了一点,当时来说,已经比较持平了。又一再强调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也是当时大家的共识。文章不长,不到千字,标题为《巩固成果坚持斗争》。我笔录完毕,读一遍给他听,未有改动,就定稿了。 这本纪念册清样拿到手时,华东戏曲研究院的改组改建工作已完成,原单位秘书长已调北京,任中国剧协秘书长。看清样这最后一关落到了上海市文化局代局长陈虞孙头上。他看了清样,觉得篇幅太庞杂,把文章严加选择,改名为《华东戏曲研究院文件资料汇编》于1955年3月作为内部文件出版,印数有限。经过“**”,留下的更少了。 从1955年春天开始,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而我到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一处,不久被指定联系京剧院,我和周信芳又有了较多的晤谈机会。当昆剧《十五贯》在全国广为传播时,他一向以演清官戏《打严嵩》、《四进士》诸剧而负盛名,自然也想到编一出新的清官戏,选择什么题材,他拿不定主意。我谈起文化局领导李太成也叮嘱我要多多关心清官戏的题材,我初步提出了海瑞及至蔡襄等历史人物。周信芳说,他从前演过传统的连台本戏《德政坊》和《五彩舆》,都是以海瑞为主角,但故事则各不相同,问我这两个本子哪一种好些。我对他说,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两种本子我都看过,故事都曲折有趣,但是却和历史上的海瑞是两回事,《五彩舆》写鄢懋卿的妻子被别人抢去,那情节比较庸俗。周信芳听了,放弃了改编《德政坊》或《五彩舆》的想法。 我收集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的工作得到了李太成的肯定,周信芳又对海瑞戏流露了浓厚的兴趣,我更加快了工作的进度。1957年初,我已经把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两代各种海瑞的文集读完,整理出了一本简要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很快审查通过,出版问世了。 1959年4月9日,周扬在上海传达中宣部宣传海瑞精神的决定,希望上海文艺界能创作、上演宣扬海瑞刚正不阿精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正因为我写过《海瑞》传记,一时之间成了许多报纸、刊物乃至文艺单位以及电影厂的访问、约稿对象。 《解放日报》约我写稿,因为是党报,我也就没有向李太成汇报,径自为其副刊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南包公海瑞》。周信芳本人以及上海京剧院根据权威方面的意见就以《南包公海瑞》的故事框架开始酝酿写京剧,并约我到院部艺术室作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报告,院长周信芳、副院长陶雄、编剧许思言都去听了。我发现图书资料室贴了一张布告,可以代购《海瑞》一书。 上海京剧院的《海瑞上疏》(初名《海瑞上本》)由周院长亲自在抓,而且在名义上还请《文汇报》社长陈虞孙“挂帅”,后来很少来找我。文化局干部的分工经常在调动,当时有数千万字的传统剧目要校勘,急等着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临时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班子,调我协助宗政文一起负责。从此,我和《海瑞上疏》不再有联系,正式公演时,报刊还是约我写了剧评。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的周密安排之下在《文汇报》发表,随之吴晗作了自我批评。《文汇报》从此就直接由**控制了。《文汇报》出面组织了两次讨论,出席者都是学术界的。我去了,未见周信芳。但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召开几次大规模的会议,周信芳去了。杨永直部长强调了讨论不必和《海瑞上疏》联系,我们稍稍放心一些。 很快,徐景贤受**指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服务,》,那是1966年2月12日,黑文咬定我和吴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然还未点周信芳的名,但此文咬定《海瑞上疏》为《海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我们已经感觉到一场弥天大祸要降临了。 上海的剧协也召开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座谈会,基本上由姚时晓主持,周信芳和我每次都参加了。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仍是从戏曲史的角度谈问题,心平气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冯树棠每次发言都无限上纲上线,有时比丁学雷那篇黑文更杀气腾腾。周信芳每次都气得脸色发白,甚至身体打哆嗦。我的发言更毫无例外地被冯树棠批得体无完肤。主持人姚时晓竭力想把讨论会的批斗倾向扭转过来,可毫无作用,最后成了道地的斗批会,只是没有打人而已。 4月间,我被宣布“靠边”,据说是第一个“靠边”的。两周后,有了第二个“靠边”的,就是周信芳。紧接着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会,有时接连着好几天,天天都有,在单位、在工厂、在剧场各地的都有。《海瑞上疏》是周扬指定、指导的剧目,我们都认为是完成党所布置的任务。当造反派“揭露”周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我们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声辩的余地了。 而且,陶君起编辑出版《京剧剧目初探》,也要举行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陈大,改编过《四郎探母》,也要举行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足见**、姚文元、徐景贤等人必欲把周信芳和我置之死地才甘心了。在这些批斗会中,一连三四小时不准抬头,不准喝水,尤其在大热天,真是惨无人道。下午开批斗会的话,没有晚饭吃,也是当时不成文的法。 《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好,《海瑞上疏》的批判也好,原是“四人帮”**夺权的开锣戏,后来他们忙于别的重大政治阴谋,这种批斗会就少开了。彼此又不在一处“隔离”,我和周信芳见面的机会随之减少。我被解除“隔离”不久,又到了五七干校。在监督劳动中,又怎敢打听周信芳的下落呢, 周信芳于1975年3月8日因受长期残酷迫害而死于华山医院一事,我于1978年回到市文化局以后才知道。 8月16日,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在龙华革命公墓进行。一位科级干部指派我用墨笔工整楷书写了所有的通知的信封,有的曾经“造反”的好汉也参加了。但他不准我参加。 11月,上海市文化局与剧协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为周信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为与《海瑞上疏》有关的、受到诽谤的、迫害的一批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了大规模的座谈会,为受迫害而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死的李平心、周信芳等平反昭雪。社联负责人罗竹风派副秘书长郑心永事先来看我,要我对出席人员提出意见。我认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及其夫人在“**”中遭遇甚惨,目前精神上仍痛苦不堪,请考虑邀请出席。罗竹风采纳了我的建议。在讨论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同志也作了发言,我冒昧地向夏老说,周信芳家属也在会场,希望他能接见。夏老一口应允,随即与周少麟夫妇进行了单独的会晤,亲切地慰问。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总觉得很愧对这位成就卓越、含冤而死的大艺术家。 这些年来,已经写了几篇关于周信芳的回忆文章,都是亲身经历,相信有许多事情是从未披露过的。这一篇文章不长,却是比较全面地回忆了我们相处的旧事,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范文二:我和冯志远相处的日子
1963年6月24日,冯志远(右二)、李术培(右一)与鸣沙中学部分师生合影。
◎叶建功
编者按:李术培和冯志远1957年同在上海第一速成师范教书,又一同于1958年从上海支宁到中宁县鸣沙中学教书至1973年分开,相处16年。如今,他二人都已过古稀之年,望着50年前风华正茂的合影,叹岁月不居,人生易逝。然令人欣慰的是,冯老师感人事迹已家喻户晓,李术培就报刊、电影已报道展现的事迹外,作一拾遗回忆。
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李术培拿着报名单来到宁夏驻上海办事处请求到宁夏去,办事处门口挤满了人,冯志远也在报名队伍中。
由于获得批准支边的人太多,李术培设法搭乘了普陀区支边的列车。上车后,年轻人很快打成一片。在聊天中,李术培得知冯志远这位东北师大毕业生和刚结婚的妻子有一套住房,这在上海都是令人羡慕的生活,冯志远却愿意放弃优裕的生活到边远山区,精神令人敬佩。俩人聊起到西北的生活时,冯志远说:“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一切就好坦然面对了。”
10月21日,火车终于到达银川。
同校教书
到达银川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术培他们被安排到郭家庄 (现银川黄河西路转弯至满城街)劳动锻炼修路,干了一冬天。1959年,李术培和冯志远先后分配到中宁县鸣沙中学教书。
当时教室和宿舍都是土平房,教室黑板是用水泥掺锅黑抹平刷黑板漆而成,粉笔是教职工用石膏自制的,较硬易断,写出的字是灰白色的。因为缺老师,冯志远代语文、俄文、历史、地理课,有时还代音乐、生物。他教学特认真,备课、讲课、辅导学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早晨5点起床,夜里12点休息是他多年的习惯。只要李术培晚上去找冯志远聊天,就会看到他在自制的煤油灯下埋头批改作业,学生作业空白处写满了批语,凡是错别字都更正过来,冯志远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孩子们围着他问这问那了。
一天晚饭后,李术培和冯志远两人沿着校外七星渠坝散步,冯志远指着渠对李术培说:你别小看了这条渠,它的历史可悠久了,早在明朝朱元璋第16子朱旃任宁夏庆靖王时主编的《宁夏志》中就已写过——七星渠、羚羊渠在黄河东鸣沙州界。李术培听了深为震惊,叹服冯志远的渊博学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师生们敬重冯志远的同时,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因为他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物困难,有的老师便骑车去县城买来质量好些的粉笔,用柳条制教鞭给他用。有时生产大队演电影,学生们牵着他的手往返,冯老师就恢谐地说:“再带上二胡,就是瞎子阿炳了。”
困难时期的“冯傻子”
1960年,鸣沙中学的师生们开始经历粮食低标准的困难日子,为补充口粮不足,学校组织大家挖野菜,开荒种地。冯老师婉谢了领导照顾,事事参加。因眼疾常辨认不清野菜,但又毫不示弱多挖野菜,回校后,再经师生帮助拣出杂草,将野菜分类。到了冬闲的时候,他就冒着严寒去牛首山张恩堡新田大队扫盲,坐在农家热炕上,屋里围满了农民兄弟,大家学习很认真,都说冯老师教人有一套,像讲故事。
低标准时期大家都饿肚子,冯老师爱人尽力从上海邮寄些食品给他,但每次寄来他即打开邮包分给师生们一起吃,什么饼干、鱼干、水果糖、藕粉等,食堂的炊事员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冯傻子。
冯老师平日不善料理生活,冬天一次煤烟中毒差点要了命,幸亏师生发现及时,在喝了学生从家里端来的酸菜汤后才缓了过来。后来其他老师帮忙重新砌了炕,套了炉子,使烟道通畅,炕也热乎多了。
排演歌剧
在和冯志远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李术培深感其为人诚实、正真,心胸坦荡。
“**”时学校停课,冯志远总觉得不干点工作心里空荡荡的,便和李术培一起将样板戏《沙家浜》改编成歌剧。几经修改剧本终于完稿,他俩又分头物色演员,挑选有表演才能的学生排练。本着不花钱也办事的原则,他们号召大家自己绘制道具,演出服也是动员大家用旧衣服拆洗改制成的,而乐队则是从会演奏的师生和周围农民中挑选组建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歌剧终于出炉了,在之后的全校演出和其他学校演出受到了极大欢迎。随后,各生产队、公社纷纷邀请他们出演。于是,他们套上毛驴车、用自行车驮上道具,到周边的鸣沙、恩和、白马、长滩等巡回演出,所到之处社员趋之若鹜。一时哄动了中宁县。
2007年国庆长假时,在银川的师生返中宁叙旧,当时的学生曹建民还将保存了30多年的《沙家浜》手抄剧本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回忆往事。
他日剪烛
李术培至今对1972年的中秋节记忆犹新。那天傍晚他与冯志远散步,校外蜿延流淌的渠水、枣树林,还有起伏的小山坡,很美的乡村景色,收获的秋季是一片金黄的瑰丽色块。对此美景冯志远缓缓说道:“我愧对妻儿啊。”李术培很理解他的心情,除了每年假期回沪探亲外,他从未请过假回过上海。妻子马毓仁教学工作也很繁忙,又患有糖尿病,体质较弱,形单影只支撑家庭,出现任何难事只能一人承受。孩子曾患急病住院,冯志远也因教学忙而无力向千里之外的妻儿伸出援手。他们夫妻俩多年的两地分居,几次有调动机会,冯志远也都放弃了。他常常自责没尽丈夫、父亲的责任,孩子文科差于理科,亦无法辅导,他在无尽牵挂中以诗排遣:“曾夫千益无一得,硕果仅存在九实”(独子名冯九实)。
冯志远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清贫谦然,永远的默默奉献,就像西北沙漠的红柳。后来人会把他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牢牢铭记在心。
征稿启事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生活、你周围的人和事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报即日起征集能够反映这50年来生活变化的照片和文章。征集的照片可以是展现宁夏风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的面貌。要求展现宁夏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让50年中的各个精彩瞬间永远被铭记;征集的文章要求必须是真实的故事,记录这50年来,你所经历的故事或者事件,以及难以忘却的记忆。要求: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事实准确,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不要虚构和面面俱到。字数2000字左右,重大题材不超过3000字。所选文章及照片,我们将陆续刊发在本版“细数50载———民间记忆”栏目中。
联系人:李晓睿
电话:0951—6037680
电邮:xinxiandeemail@163.com
邮寄:银川市中山南街47号《新消息报》专刊部“岁月之河”收(750004)
范文三:与鬼魂相处的日子 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青年时期的我极少接触京剧,1940年冬天,我因孤岛形势日益恶化,决定离开上海去大后方。动身前,中学同学王南群、过振东为我送行,请我在卡尔登大戏院观看了周信芳演出的《文素臣》。周信芳、高百岁等著名艺术家的表演精彩纷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我整整9年没再观看过京剧。
194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那时天天看戏,工作往来中也常能见到周信芳,却没有个人间的交往。1950年5月,华东文化部成立,我调到戏改处,不久就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周信芳出任院长。于是,我和周信芳打交道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
1951年,中国戏曲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吕君樵、张震和我负责初试,录取了生行的钱浩梁(浩亮)和旦行的马晨曦。复试时,校方请到梅兰芳、周
1
信芳做主持,我作为行政人员也到了场。对周信芳这样的名表演艺术家而言,这确是小事一桩,他推说事情忙,不来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考试那天,他还是如约到达,而且来得很早——他平日就常来衡山路10号。开考后,有考生唱《追韩信》,我怕作为考官的他会有想法,便解释道:“考生们事先根本不知道谁来对他们进行复试。”周信芳笑了笑,不以为然:“他们不一定要唱我的戏啊~”听了钱浩梁的唱段后,周信芳表示基本满意,只是认为他嗓子不太好,这是青春期常有的现象,很快会好转的。钱退场后,他表示可以录取,又对我说:“原来这是钱麟童的儿子,他父亲我熟悉。”这次的复试工作,在我和周信芳相处的短短两小时里,他办事的认真细致,对青年的爱护有加,都出乎我意料。当然,梅兰芳也准时到达了,对于旦角的考试,也极其认真细致。
1953年,华东文化部改组为华东文化局,我到华东戏曲研究院从事资料研究工作。时任院长的周信芳每次来到院部,如果不是有会要开,总是毫不例外地先到资料研究组兼作图书室的大厅,或与大家攀谈,或翻阅图书。关于京剧唱、念、做、打诸问题,他基本上找徐筱汀(著名戏剧理论家、戏曲教育家徐慕云之弟)聊,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则喜欢与我探讨。我们常在一起谈论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剧目,发现彼此都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共同语言很多。周信芳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
2
教育,7岁时便以“七龄童”的艺名而蜚声京剧舞台,对文史学术有这样的基础,使我倍感意外,也颇为钦佩,没有对真知孜孜以求的恒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一批戏剧艺术表演家,有如此才华和底蕴的,真可谓凤毛麟角。
那时中央文化部、中国京剧院、中国戏剧出版社都忙着剧目审订工作,决定先把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的代表作予以整理出版和推广,也是对所有戏曲表演艺术界剧目审订工作的推动和示范。北京经常来文来电催促,不仅如此,有时还派戴不凡(曾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到上海,工作抓得很细、很具体。有一天,周信芳约我单独谈话,说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定稿问题。他拿出亲笔写下的手稿,实际就是当时的演出本,还有一份田汉对三四句唱词的修改意见。周信芳说:“这些现在都交给你,请你替我拿个主意,把本子定下来。”我心下忐忑:这个本子在舞台上演出多年,已成为经典,岂是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可以轻举妄动的,至于田汉,他是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局长,既是戏曲权威,也极在行。因此我一再推辞,但周信芳却不肯改变决定。我又说:“也许院里编审室的京剧组更适合做这件事。”他严肃认真地说:“在京剧业务方面,他们比你熟悉,但是对《史记》《汉书》等,你比他们熟。这是历史剧,还是请你拿主意比较合适。”就这样,我有点诚惶诚
3
恐地把任务接了下来,用心钻研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交还了本子。最终是否采用了田汉的意见已记不清,但这对我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先后两年多,我和周信芳的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主演的戏,我印象颇深的除了《四进士》《萧何月下追韩信》《打严嵩》《清风亭》《坐楼杀惜》外,还有《秦香莲》。其中《秦》的本子集中了各剧种本子之精华,执笔者为严朴,但其实也可以说是周信芳亲自改编的,因为其中的字句均出于他的口述,严朴仅为“执笔”而已。《秦香莲》演出时,周信芳一人饰两角,前为丞相王延龄,后为开封府尹包拯。王延龄为一熟悉世故人情近乎圆滑之老官僚,但尚存一些正义感,可又怕担风险,人物多面,性格复杂。周信芳塑造的王延龄恰到好处,与《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形之下,包拯反倒显得较为一般,唱腔并未向净角靠拢,但尽可能淡化了迷信色彩,加重了人情味。该剧的彩排、公演与华东会演,我看了三次。后来,我向周信芳提了个问题:王延龄身为丞相,他解决不了这个案子,却让秦香莲去向开封府告状,于情于理似乎说不通——开封府尹的官固然不小,但总也比不过丞相啊。周信芳听后也笑了:“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老戏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首先这样处理的。你的疑问我也早想到了。戏这样编,不能说明它荒唐离谱,实际多少也是有一点依据和由来的。我查阅了
4
《宋史》,原来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没做皇帝之前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开封府尹的职权实际上已超越了法律文本所规定的范围,而仅次于皇帝了。”我去翻阅了《宋史》,果然如此,内心暗暗叹服,对他更为钦佩。1961年,北京、上海都为“周信芳舞台生活60周年”开展庆祝活动,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略谈周信芳的史学修养》,也谈到了他关于《秦香莲》、关于包拯的谈话。
十分遗憾的是,周信芳的《秦香莲》后来极少有人谈起,这一版本的演出更成了绝响。能够前面化身王延龄,后面化身包拯这样一人饰两角的表演艺术家,恐怕也难找了。那时,我还和周信芳一起在台下看过金素雯、陈正薇、沈金波诸人合演的《皇帝和妓女》,记得看后他发表了感慨:“像范琼这种类型的坏人,肯定现在也会有,当然不多。只是他们隐藏得很深,不容易让人发现罢了~”也许他话中有话,”坏人”也另有所指,但我没有追问。
1955年时,随着华东大区的撤销,华东戏曲研究院也不存在了,同时分别成立了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戏曲学校等机构。从1955年春天开始,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而我到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一处,不久被指定联系京剧院,我和周信芳又有了较多晤谈的机会。当时昆剧《十五贯》在全国广为传播,周信芳一向以演清官戏(如《打严
5
嵩》《四进士》等剧)而负盛名,自然也想要编一出新的清官戏。但至于选择什么题材,他拿不定主意。闲谈时,我说起文化局领导李太成也叮嘱我要多关心清官戏的题材,已初步提出可选用的海瑞及至蔡襄等历史人物。周信芳说,他从前演过传统的连台本戏《德政坊》和《五彩舆》,都是以海瑞为主角,但故事则各不相同,问我这两个本子哪个好些。我说这两种本子我都看过,故事都曲折有趣,但和历史上的海瑞却是两回事,《五彩舆》写鄢懋卿的妻子被别人抢去,情节比较庸俗。周信芳听后,放弃了改编《德政坊》或《五彩舆》的想法。 我收集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的工作得到了李太成的肯定,周信芳又对海瑞戏流露出浓厚的兴趣,我更加快了工作进度。1957年初,我已把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两代的各种海瑞文集读完,整理出了一本简要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书目通过了审查,很快便出版问世了。
1959年4月9日,周扬在上海传达中宣部宣传海瑞精神的决定,希望上海文艺界能创作、上演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精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因为我写过《海瑞》传记,一时间成了许多报纸、刊物、文艺单位以及电影厂访问、约稿的对象。《解放日报》约我写稿,因为是党报,我也就没向李太成汇报,径自为其副刊写了一篇约5000字的《南包公海瑞》。周信芳及上海京剧院根据权威方面的意见,就以《南
6
包公海瑞》的故事框架开始酝酿写京剧,并约我到院部艺术室作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报告。
上海京剧院的《海瑞上疏》(初名《海瑞上本》)由周院长亲自在抓,而且名义上还请到了《文汇报》社长陈虞孙“挂帅”。当时的文化局干部经常调动,因有数千万字的传统剧目要校勘,急等着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上级临时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班子,调我协助宗政文一起负责。于是,从此我与《海瑞上疏》不再有联系。
转眼到了l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的周密安排下,发表于《文汇报》,随之吴晗作了自我批评。《文汇报》就此直接由**控制了,报纸出面组织了两次讨论,出席者都是学术界的人物,我也去了,不过未见到周信芳。联想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几次大规模会议,周信芳都去了,我觉得有点诧异。但杨永直部长强调讨论不必和《海瑞上疏》联系,我们才稍放心一些。
很快,1966年2月12 日,徐景贤受**的指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服务,》,“黑文”咬定我和吴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然还未点周信芳的名,但此文咬定《海瑞上疏》是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我们感到一场弥天大祸就要降临了。
7
上海剧协也召开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座谈会,基本上由姚时晓主持,周信芳和我每次都参加了。会上,虽然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仍是从戏曲史的角度谈问题,心平气和,但上海戏剧学院的某青年教师每次发言都无限上纲上线,有时比丁学雷那篇“黑文”更杀气腾腾。周信芳每次听了都气得脸色发白,甚至身体打哆嗦。我的发言也毫不例外地被批得体无完肤。主持人姚时晓竭力想把讨论会的批斗倾向扭转过来,可毫无作用,最后成了道地的批斗会,只是还没发展到打人而已。4月间,我被宣布“靠边”,据说是第一个“靠边”的。两周后,有了第二个“靠边”的,那就是周信芳。紧接着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会,有时接连着好几天,在单位,在工厂,在剧场各地开的都有。《海瑞上疏》是周扬指定、指导的剧目,我们都认为是完成党所布置的任务,当造反派“揭露”周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我们当然已没有任何申辩的余地。在这些批斗会中,一连三四个小时不准抬头,不准喝水,尤其顶着大热天,其情形可谓惨无人道。
《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好,《海瑞上疏》的批判也罢,原是“四人帮”**夺权的开锣戏,后来他们忙于别的重大政治阴谋,这种批斗会就少开了。彼此不在一处“隔离”,我和周信芳见面的机会随之减少。我被解除“隔离”不久,又到了五七干校。在监督劳动中,我又怎敢打听周信芳的下落呢,
1975年3月8 日,周信芳终因受长期残酷迫害而死于
8
华山医院。我于1978年回到市文化局后,才知道他的死讯。当年8月l6日,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一位科级干部指派我用楷书写了所有通知的信封,有些曾是“造反派”的同志也参加了,但我仍不在应准的行列。
11月,上海市文化局与剧协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为周信芳,也为与《海瑞上疏》有关的受诽谤、迫害的一批同志恢复名誉。与此同时,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也召开了大规模的座谈会,为受迫害而死的李平心、周信芳等平反昭雪。社科联负责人罗竹风派副秘书长郑心永事先来看望我,问我对出席人员有何意见。我认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及其夫人在“**”遭遇甚惨,目前精神上仍痛苦不堪,请组织考虑邀请他们出席。罗竹风采纳了我的建议。在讨论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夏征农也作了发言,我冒昧地对夏老说,周信芳家属也在会场,希望他能接见。夏老随即与周少麟夫妇进行了单独的会晤,并作了亲切慰问。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总觉得愧对这位成就卓越、含冤而死的大艺术家。
多年后记录下这些文字,篇幅虽不长,却较全面地回忆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旧事,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作者系戏曲史家、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9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
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10
范文四:[精品]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青年时期,我极少接触京剧。1940年冬天,我因孤岛形势日益恶化,决定离开上海去大后方。中学同学王南群、过振东为我送行,请我在卡尔登观看了周信芳的《文素臣》,周信芳、高百岁诸位的表演很精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整整九年,没有再观看过京剧。 194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那时天天看戏,也经常见到周信芳,但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1950年5月,华东文化部成立,我调到戏改处,不久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周信芳出任院长,我和周信芳打交道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1951年,中国戏曲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吕君樵、张震和我负责初试,录取了生行的钱浩梁和旦行马晨曦。复试请梅兰芳、周信芳主持,干部则仅我一人到场了。周信芳经常来衡山路十号,因为来得较早,我们就随便谈开了。后来考生唱的戏是《追韩信》,周信芳笑了,他说:“不一定要唱我的戏啊~”我向他作了解释:“事先考生根本不知道谁来对他们复试。”周信芳听了钱浩梁(浩亮)的唱,基本上表示满意,认为嗓子不太好,是青春期常有的现象,很快会好转的,于是,他又问了这个考生一些其他问题。考生退场,他表示可以录取,又对我说:“原来是钱麟童的儿子,他父亲我熟悉。”这一次复试工作,我和周信芳一起两个小时,对他的办事认真细致、对青年的爱护都有了出乎意料的体会。因为对周信芳这样的名表演艺术家来说,这确是小事一桩也。他推脱事情忙,不来,也完全可以。当然,梅兰芳也准时到达了,对于旦角的考试,也极其认真细致。 就在这一年,周信芳演剧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在上海出版的特刊上有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一篇十分简短的祝词,是陈望道部长叮嘱我拟的初稿。华东文化部及所属戏改处都送了用整幅宣纸写的祝词各一轴,都是伊兵处长布置我写的颜体楷书,字相当大。因为这些只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做的工作,当然没有告诉周信芳本人我分别是拟稿者、书写者,所以周信芳始终不知道。现在那本特刊仍有收藏、流传,那两轴颜体楷书早在“**”中被毁了。 1953年,华东文化部改组为华东文化局,我到华东戏曲研究院做资料研究工作,和院长周信芳经常在一起谈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剧目,我们彼此发现都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七岁时以“七龄童”艺名而蜚声京剧舞台,对文史学术有这样的基础,使我完全出乎意外,也颇为钦佩。没有恒心和毅力,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在旧社会成长的一大批戏剧艺术表演家,像他周信芳,真是凤毛麟角也。 他每次来到院部,如果不是有会议要开,毫不例外地总是先到资料研究组兼作图书室那一个大厅,和大家谈,或翻阅图书。关于京剧唱、做、念、打诸问题,他基本上找徐筱汀(徐慕云之弟)谈,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上找我。很快,我们彼此都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那时候中央文化部、中国京剧院、中国戏剧出版社都忙着剧目审定工作,决定先把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的代表作予以整理出版,予以推广,也是对所有戏曲表演艺术界剧目审定工作的推动和示范。北京经常来文来电催促,不仅如此,有时还派戴不凡到上海,抓得很具体。有一天,周信芳却约我单独谈话,谈的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定稿问题,他拿出了当时的演出本,实际上也是他亲笔写下的手稿,还有一张纸,是田汉的意见,那是对三四句唱词有所修改。周信芳说:“现在都交你,请你替我拿个主意,把本子定下来。”因为这本子已经在舞台上演出多年,成为经典了,岂是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可轻举妄动的,至于田汉,他是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局长,既是权威,也极在行,因此我一再推辞,他却不肯改变他的决定。我又说:“院里编审室的京剧组也许比较适合做这件事。”他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京剧业务,他们比你熟悉,但是对《史记》、《汉书》,你比他们熟,这是历史剧,还是请你拿主意比较合适。”就这样,我真有点诚惶诚恐,把任务接下来了,大约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交还本子。究竟采用了田汉的意见没有,已记不清,但是,这对我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周信芳也没有再有任何反复,《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记》说明此剧由严朴、蒋星煜协助整理,严朴是编审室京剧组组长,所以也有
他的名字,实质他并未参与。 为了配合《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的发行和宣传,《光明日报》同时组织我写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人物描写》,在副刊《东风》发表,我也正好借此机会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此文后来被收入《周信芳艺术评论集》,于1982年12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后来曾再版过,剧本未有任何改动,但协助整理者姓名却变了。这种事情我经历多了,没有精力去交涉。 华东戏曲研究院那里先后两年多,和周信芳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主演的戏我印象颇深的除了《四进士》、《萧何月下追韩信》、《打严嵩》、《清风亭》、《坐楼杀惜》之外还有《秦香莲》,这个本子集中各剧种本子的精华,执笔者为严朴,但也可以说是周信芳亲自改编,字字句句均出于他的口述,严朴“执笔”而已,采取了包审包断的框架。周信芳一人饰两角,前为丞相王延龄,后为开封府尹包拯。王延龄为一熟悉世故人情近乎圆滑之老官僚,但还有一些正义感,可又怕担风险,性格复杂。周信芳塑造之王延龄恰到好处,与《四进士》之宋士杰异曲而同工。相形之下,包拯反而比较一般,唱腔并未向净角靠拢,但尽可能淡化了迷信色彩加深了人情味。彩排、公演、华东会演,我看了三次。我向周信芳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延龄身为丞相,他解决不了的案子,叫秦香莲去向开封府告状,于情于理似乎说不通。因为开封府尹的官固然不小,但总比不过丞相也。周信芳听了也笑了,他对我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老戏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首先如此处理的,但是,你的疑问我也早就想到了。戏这样编,不能说它荒唐离谱,多少也有一点依据,或者说有由来的。我查阅了《宋史》,原来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赵恒没有做皇帝之前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当时人们心目中,这开封府尹的职权实际上已超越了法律文本所规定的范围,而仅次于皇帝了。”我去翻阅了《宋史》,果然如此,从此对他更加钦佩。1961年,北京、上海都为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周年而展开了庆祝活动,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略谈周信芳史学修养》,2月2日发表于该报,也谈到了他关于《秦香莲》、关于包拯的谈话。 十分遗憾的是周信芳的《秦香莲》也极少有人谈起,这一版本的演出更成了绝响,能够前王延龄、后包拯这样一人饰两角的表演艺术家恐怕也难找了。 我还和周信芳一起在台下看过金素雯、陈正薇、沈金波诸人合演的《皇帝和妓女》,他发表了感慨,他说:“像范琼这种类型的坏人,肯定现在也会有,当然不多。隐藏得很深,不容易发现罢了~”也许他有所指,我没有追问。 随着华东大区的撤销,1955年华东戏曲研究院也将不存在,同时分别成立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戏曲学校等机构。许多同志建议:出版一本纪念册。秘书长伊兵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落实了这件事情:一、院长周信芳以及院内各级领导和主要编、导、演、音乐、舞美都写点经验或心得体会;二、为了不影响机构改组、移交等工作,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作组,在上海越剧院内辟一室作为办公室。这一切都异常顺利地在进行。 这个工作组共三人,伊兵指定以我为主。我立即和周信芳院长联系,他一口答允,但他说了大意,要我成文。作为工作总结的第一篇,主要是谈对戏曲遗产的看法,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一概否定,但也应该允许作某些改动。所用的语言从现在来看,也许“左”了一点,当时来说,已经比较持平了。又一再强调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也是当时大家的共识。文章不长,不到千字,标题为《巩固成果坚持斗争》。我笔录完毕,读一遍给他听,未有改动,就定稿了。 这本纪念册清样拿到手时,华东戏曲研究院的改组改建工作已完成,原单位秘书长已调北京,任中国剧协秘书长。看清样这最后一关落到了上海市文化局代局长陈虞孙头上。他看了清样,觉得篇幅太庞杂,把文章严加选择,改名为《华东戏曲研究院文件资料汇编》于1955年3月作为内部文件出版,印数有限。经过“**”,留下的更少了。 从1955年春天开始,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而我到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一处,不久被指定联系京剧院,我和周信芳又有了较多的晤谈机会。当昆剧《十五贯》在全国广为传播时,他一向以演清官戏《打严嵩》、《四进士》诸剧而负盛名,自然也想到编一出新的清官戏,选择什么题材,他拿不定主意。我谈起文化局领导李太成也叮嘱我要多多关心清官戏的题材,我初步提出了海瑞及至蔡襄等历史人物。周信芳说,
他从前演过传统的连台本戏《德政坊》和《五彩舆》,都是以海瑞为主角,但故事则各不相同,问我这两个本子哪一种好些。我对他说,两种本子我都看过,故事都曲折有趣,但是却和历史上的海瑞是两回事,《五彩舆》写鄢懋卿的妻子被别人抢去,那情节比较庸俗。周信芳听了,放弃了改编《德政坊》或《五彩舆》的想法。 我收集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的工作得到了李太成的肯定,周信芳又对海瑞戏流露了浓厚的兴趣,我更加快了工作的进度。1957年初,我已经把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两代各种海瑞的文集读完,整理出了一本简要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很快审查通过,出版问世了。 1959年4月9日,周扬在上海传达中宣部宣传海瑞精神的决定,希望上海文艺界能创作、上演宣扬海瑞刚正不阿精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正因为我写过《海瑞》传记,一时之间成了许多报纸、刊物乃至文艺单位以及电影厂的访问、约稿对象。 《解放日报》约我写稿,因为是党报,我也就没有向李太成汇报,径自为其副刊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南包公海瑞》。周信芳本人以及上海京剧院根据权威方面的意见就以《南包公海瑞》的故事框架开始酝酿写京剧,并约我到院部艺术室作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报告,院长周信芳、副院长陶雄、编剧许思言都去听了。我发现图书资料室贴了一张布告,可以代购《海瑞》一书。 上海京剧院的《海瑞上疏》(初名《海瑞上本》)由周院长亲自在抓,而且在名义上还请《文汇报》社长陈虞孙“挂帅”,后来很少来找我。文化局干部的分工经常在调动,当时有数千万字的传统剧目要校勘,急等着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临时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班子,调我协助宗政文一起负责。从此,我和《海瑞上疏》不再有联系,正式公演时,报刊还是约我写了剧评。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的周密安排之下在《文汇报》发表,随之吴晗作了自我批评。《文汇报》从此就直接由**控制了。《文汇报》出面组织了两次讨论,出席者都是学术界的。我去了,未见周信芳。但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召开几次大规模的会议,周信芳去了。杨永直部长强调了讨论不必和《海瑞上疏》联系,我们稍稍放心一些。 很快,徐景贤受**指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服务,》,那是1966年2月12日,黑文咬定我和吴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然还未点周信芳的名,但此文咬定《海瑞上疏》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我们已经感觉到一场弥天大祸要降临了。 上海的剧协也召开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座谈会,基本上由姚时晓主持,周信芳和我每次都参加了。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仍是从戏曲史的角度谈问题,心平气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冯树棠每次发言都无限上纲上线,有时比丁学雷那篇黑文更杀气腾腾。周信芳每次都气得脸色发白,甚至身体打哆嗦。我的发言更毫无例外地被冯树棠批得体无完肤。主持人姚时晓竭力想把讨论会的批斗倾向扭转过来,可毫无作用,最后成了道地的斗批会,只是没有打人而已。 4月间,我被宣布“靠边”,据说是第一个“靠边”的。两周后,有了第二个“靠边”的,就是周信芳。紧接着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会,有时接连着好几天,天天都有,在单位、在工厂、在剧场各地的都有。《海瑞上疏》是周扬指定、指导的剧目,我们都认为是完成党所布置的任务。当造反派“揭露”周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我们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声辩的余地了。 而且,陶君起编辑出版《京剧剧目初探》,也要举行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陈大,改编过《四郎探母》,也要举行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足见**、姚文元、徐景贤等人必欲把周信芳和我置之死地才甘心了。在这些批斗会中,一连三四小时不准抬头,不准喝水,尤其在大热天,真是惨无人道。下午开批斗会的话,没有晚饭吃,也是当时不成文的法。 《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好,《海瑞上疏》的批判也好,原是“四人帮”**夺权的开锣戏,后来他们忙于别的重大政治阴谋,这种批斗会就少开了。彼此又不在一处“隔离”,我和周信芳见面的机会随之减少。我被解除“隔离”不久,又到了五七干校。在监督劳动中,又怎敢打听周信芳的下落呢, 周信芳于1975年3月8日因受长期残酷迫害而死于华山医院一事,我于1978
年回到市文化局以后才知道。 8月16日,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在龙华革命公墓进行。一位科级干部指派我用墨笔工整楷书写了所有的通知的信封,有的曾经“造反”的好汉也参加了。但他不准我参加。 11月,上海市文化局与剧协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为周信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为与《海瑞上疏》有关的、受到诽谤的、迫害的一批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了大规模的座谈会,为受迫害而死的李平心、周信芳等平反昭雪。社联负责人罗竹风派副秘书长郑心永事先来看我,要我对出席人员提出意见。我认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及其夫人在“**”中遭遇甚惨,目前精神上仍痛苦不堪,请考虑邀请出席。罗竹风采纳了我的建议。在讨论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同志也作了发言,我冒昧地向夏老说,周信芳家属也在会场,希望他能接见。夏老一口应允,随即与周少麟夫妇进行了单独的会晤,亲切地慰问。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总觉得很愧对这位成就卓越、含冤而死的大艺术家。 这些年来,已经写了几篇关于周信芳的回忆文章,都是亲身经历,相信有许多事情是从未披露过的。这一篇文章不长,却是比较全面地回忆了我们相处的旧事,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范文五:从“三伏贴”想起我和中医相处的日子
作者:虫吟草深
方舟子的《三伏贴是种“荒唐的做法”》一文,使我想起了我年轻时患过敏
性哮喘时看中医的经历,之中就有文中所说的在三伏天敷贴,驱寒来治疗哮喘。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大房间,好几排长条的撘起来的卧榻,上面铺着
草席,我们都被护士告诉要脸朝下,背朝上地躺着,小孩据多,记不起是不是有
大人了。按医生说法,敷贴必须是在夏天的大伏天,还在正午开始,那时拔寒效
果最好。在江南一带,梅雨过后,就是伏天了。那是上海最热的天。敷贴用的药
是做成一种像饼的形状的湿漉漉的东西,医生说是弄碎了的老姜,中间还放有珍
贵的麝香,都是些所谓去寒的。这东西在背部好像是左右对称地要放六个。记不
得具体要放多长时间,反正超过四个小时吧。有的人敷贴的地方会起泡,大多数
人皮肤会发红,发痒。由于是孩子,家长都陪着。口干了给些水喝。条件好点的,
喝大人给准备的西瓜汁。还记得明亮的窗外是赤日炎炎,知了(蝉)在使劲地叫
唤。对不满十岁,喜欢抓知了的我,不提有多大的吸引力了。自己只能趴着一动
不动,汗流夹背,形同受刑。记得这样的敷贴每年有一次,一共连续了三年。这
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发生的事。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是有名
的上海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稍后这地方改名为曙光医院,仍然是中医学院的附
属医院。医院中的主治医生,都是中医学院的教授或副教授。记得很清楚的是当
时该医院有一个哮喘专科门诊,每周只有对外一天。负责的医生叫徐小舟,一位
很和蔼的人。由于我的症状比较严重,且典型,似乎成了徐医生的研究对象,他
嘱咐我按时就诊,每次是事先预约好,那就不用排队了。我持续地就诊有好几年,
好像是每两周一次。
我是比较典型的过敏体质,大约一,二岁开始,满头发出“奶癣”,被父亲
戏称“小瘌痢头”。据说当时有一位有名的小儿科医生告诉母亲,这孩子将来可
能会有气喘病,不幸被他言中了。四岁左右,我开始发哮喘,从此一发不可收,
直至二十多岁。我的哮喘的发作,一年中,除了夏天,几乎没有大的间断。上海
的气候,每年九月中旬,通常会有一场秋雨,雨后天气立马转凉,人们穿起了长
袖,我的受难日就开始了。有时哪怕是一小小的诱因,譬如棉被的花衣纤维,都
会引起发作,有时根本没感到是什么原因。先是一连串喷嚏,眼泪鼻涕,然后就
喘起来了。最可怕是闻到新加了煤球或煤饼的炉子的味道,百发百中。一闻到,
连眼泪鼻涕都省了,直接就喘起来。回忆起来,当过一个夏天后,正当感觉身体
有点小劲,和正常的孩子差不多了,初次发作就来了,身体忽而就像被掏空一般。
我的国庆节不是在医院,就是坐在家里床上度过的。诱发哮喘的原因各人各样。
有一次看病时碰到一个病友小女孩,她妈妈告诉我们,一次家里买了大闸蟹,蒸
熟后女孩馋不过,偷偷掀开一只蟹的上壳,只是闻了那股热气,发作了三天三夜。
五十年代国内还没有像肾上腺素那样可控制发作的药物。每次喘得厉害了,
嘴唇,指甲呈较深的紫色,严重时,据家里人说床都在抖动,就不得不到医院去
挂急诊。到了医院后,两件事:接氧气和注射胺茶碱(早先还有麻黄素)。胺茶
碱,这东西打入身体后,立即就觉得心像要从口中蹦出来,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的
舒缓,但是还是比喘得厉害好些。幸好出生在大城市,如果生在缺医少药的地方,
还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的哮喘病,给家里必定是添了大麻烦,当时西医没
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就像上面写的改向中医求救了。每次看过中医,结果是一大
包的草药,煎起来味道不好闻,记得其中总有石膏一类的东西,使药汤似乎变得
更稠,吃起就更难了。当时的第十一人民医院的哮喘专科,还自主开发了针对哮
喘的成药,想得起的有鹅颈(气管)粉和用大瓶装的羊肺汤,如今还有羊肺汤极
为难喝的印象。现在看来这些药的出笼是源于吃啥补啥的理念。鹅颈这么长,还
能透气,鹅的气管定能补气管,吃肺汤补肺,猪肺太普遍,就来个羊肺!后来虽
然不去就诊了,徐医生还寄来病情追踪的表格,继续研究我。由于被列为了研究
对象,一有新药,还会有通知来。记得曾到医院去打过“鸡血针”和“地龙(蚯
蚓)注射液”。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直接注射人体内,有可能会引起致命的过敏
反应。
除了在正规的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诊。家里还带我去看过数个“江湖郎
中”。值得一记的是去接受一位中年妇女号称的割手疗法的治疗。她的理论是说
手掌的皮下内有一块东西,是招致寒气的来源,正是寒气导致了哮喘,如果割除
后哮喘就能不发和少发了。之间她拿了一把小刀,还不是手术刀,其实就是钎脚
刀(除去脚上老皮)的那种刀,用酒精一擦,不用麻药,就在我的手掌上划开一
个口子,然后用小剪刀剪下一小块发白的肉,还拿给我们看,说就是这招致了寒
气。现在想起来那小块白肉应该是我手掌的皮下脂肪!另外家里还让我尝试了不
少民间的土方和偏方,其中竟有鼻涕虫炒蛋。遗憾的是以上所有的中医治疗,民
间偏方都没有对我起作用,到了小学毕业时,由于病情日益严重,不得不终止了
我本来就是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读书--休学了。有一件对我克服患病带来沮
丧有重要意义的事不得不提一下。一次徐小舟医生和我谈到了我的哮喘的久治不
愈。他说,我看了好多好多的哮喘病人还没看到从小发到老的,将来等你发育之
后至少你症状会大大轻减,因此不用太担心,反而是中年后得了哮喘很麻烦,往
往会伴随一生。他的话给了少年的我希望和勇气。对于中医的所谓忌口问题,徐
医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让我大胆的尝试,不要因为忌口而引起营养上的问题。
六十年代起国外开发的肾上腺素喷雾器开始在中国普及,给哮喘患者带来了福音。
怀带一个喷雾器,就不必担心即时的急性发作了。后来正像徐医生所说的,大约
到了二十多岁,哮喘就不再困扰我了。徐医生如今健在的话应该是九十多岁了。
作为医生来说,他是敬业,认真的,不像今天的那些中医,为了钱,明知无效果,
还是让病员掏腰包,而且是药开得越贵越好。中医悲剧在于在故纸堆里找答案。
今天中医这个行当,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某些不良者的欺骗工具。现代医学的日新
月异的发展,已到了分子水平哪还有中医的落脚之地?可以说我对中医持怀疑态
度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医理论中对疾病因由的那种所谓相生相克的随意附会的说法,
更是源于自小所经历的各种现在看了近于荒唐的治疗。
(XYS20120809)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回忆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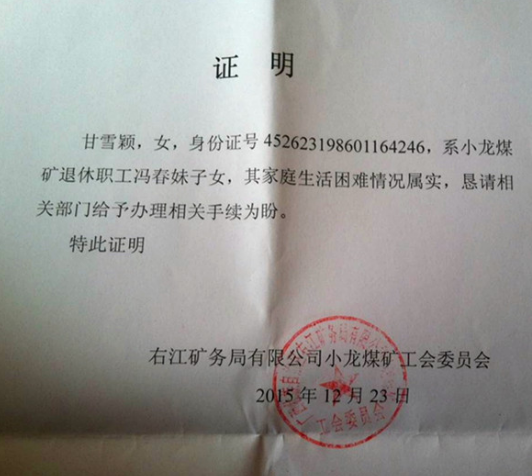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小怪兽i37508886
小怪兽i37508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