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一:祖母的秘密
[阿根廷/意大利]安·普兰德利/杜海燕(译)
身处语言相异的人海中,于我而言极富魅力。我毫不畏惧那些外语,反而挺喜欢听着丝毫不懂的语言行走在街区中。无论何时身处此境,我总会忆起祖母:她来自意大利,一战后被迫移民阿根廷。她不懂我的母语,她在阿根廷一点一滴不断学习,然而却依然更愿意说意大利语。她也给我讲意大利语。明知我听不懂,她仍然坚持。
祖母从不参加周日弥撒,她的虔诚祷告我在别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她常常深夜在房间祈祷,在一片几乎吞没了桌上台灯散发出的微弱光线的昏暗中坐在床上柔声祷告。她聚精会神又反应敏捷,她不断祷告却令人难辨始终。
我现在还能听到祖母快速小幅移动着厚厚的双唇、调节着口中气流的声音。我知道,她的祷告将永远在我耳畔回荡。我记得自己依偎在她身旁,倾听她的低语回响在温暖的房间里,声音愈来愈大,而那枯燥的祷告却容不得打断。祖母闭目轻语,偶尔睁大眼睛看我时也不会中断祈祷。她总是在晚上祈祷,但有时候上午在厨房里劳作时也会突然停下来,将自己锁在里面祈祷。
我从来都听不清她的祷告,但是祖母倾注了她无尽的信仰,因此这些声音呈现出一种精准的乐感。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也能够看出:祖母为每个玫瑰念珠赋予了她的灵魂。她没完没了发出的一个个词语配上精致的乐感,在我耳旁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低语声。语言是私密的,也是一种能上升到最高级的交流。祖母急切而富有韵律的孤独祷告,让我年幼时就明白语言双轨运行。这就是我在那些夜晚聆听完祖母祷告后的收获———发声对她来说是一种潜入内心的旅途,同时也是一种将语言送上天堂的途径,而那里一直有人在倾听。
每次忆起祖母的祷告,我都有种虽是自己母语却仍然无法理解的感觉。语言是能够部分减轻痛苦的。我彼时不懂,此时却明白了:在战争中被迫离开双亲、故园和朋友的我的祖母已痛苦不堪。她痛苦,因为她知道他们永不再见。
然而,在她那些祷告声中却并无宗教的祈祷。那是一种寻找救赎的声音,是的,一种接近绝望又坚定前行、将痛苦抛在身后的声音。但是为什么我的意大利祖母不用她的母语祈祷呢? 她常用意大利语谈论重要事情,但却从不用来祈祷。我无数次回到那般场景,思索着这两种语言,思索着她的语言选择。用意大利语的祖母很愤怒,这是她生气、诅咒、大笑和谈论秘密的语言,一种表达绝望和失落的语言。但是祷告者难道不是通过和上帝的对话记录下要事的语言吗? 用意大利语诅咒,用西班牙语祷告———这位意大利太太用了一种不属于她的语言为未来祈祷:或许她在寻找一种新的话语,或许这样她就能逃离记录了过去的空缺和迷失的语言。难道是我祖母希望未来生活会更好才用新的语言? 难道她希望使用新语法、新句法会开启崭新的生活曙光?
有时夏日午后,天气热得房间里待不住了,祖母会带我到小溪边。我们顺着一条树荫土路前行。我之所以喜欢溪流不仅因为它带来的清凉,还有那午后微风的拂水声、白杨树间的婆娑声,这都像极了我祖母的低低祈祷声。
祖母不是作家,但作为一个虔诚的人,她用新的语言、自己的韵律和独一无二清晰悦耳的声音构建了她的祷告语,然后不知不觉传给了我,并永远回响在我的耳旁。因为她,语言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内心的礼拜仪式,我知道在房间那种亲密的地方能发现语言的神圣本性:她将她深切的信仰赋予了语言。
我知道,祖母也懂得人类的存在有赖于能否识别语言中的能量,因此她有时会坚定地教我祷告。她是第一个相信语言会成为我的救赎的人。通过她传递的信息,我知道语言和沉默背后隐藏着秘密。
我们之前常去内格罗河祖父母的房子里消暑。周日我和祖母一起去河边。祖父从未想去,但有时太阳落山时他会来接我们。他一到那儿就靠在树干上,等不了太久就要和我们一起回家。祖母却仍然想在河边多待一会。她喜欢待在那儿,听风拂过水面的声音,听高大白杨树的婆娑声。我们一到那儿,祖母就脱掉鞋子,将裙子挽到膝盖上面涉足水中。她肌肤白皙,我喜欢触摸她光洁温润的胳膊。她偶尔也会掬起水,往头上洒落一些。
晶莹的水珠顺着她白皙柔软的脸颊滑落,滴到了她的脖子上。整个下午她都站在没过膝盖的水里,不介意穿着湿漉漉的紧贴着腿的裙子回家。
夜晚降临,人们逐渐入睡,我走过宽宽的门厅进入祖母的房间。门厅漆黑一片,但她门下流出的灯光指引我坚定前行。祖母睡眠极少,有时候甚至整晚都清醒,我却从未听过她抱怨。夏夜,她的窗户整晚敞开,有时我会看到她将双臂放在涂有清漆的木窗台上。温热的夜晚,她系着精致腰带的衬裙浸透了汗水,紧紧地贴在前胸和腹部。
有事么? 我打开门时她问道。
有几个夜晚,她坐在高高的床上晃动双腿,双脚微微扭动。祖父抱着枕头仰头熟睡,祖母则翻腾着一个装满写着意大利语纸张的鞋盒。她打开信件,用低沉的声音读给我听,这样不会吵醒祖父。她还给我看了一些背面有寄语的照片和意大利亲友寄来的教友卡。她轻轻读着,声音在炎热的房间慢慢升腾。后来她把所有东西重新放回盒子,藏在衣柜下面。
你祖父对此一无所知,她说。
虽然我从未发现关于那些秘密的任何事情,我也会永久守护这些秘密。写作时,我有时仿佛感觉这一切都回来了。有一种我半懂不懂的低语声在炎热的房间里飘荡;或者是寥寥几句关于那些秘密的声音。我分不出人们的声音,但是,是谁藏在衣柜下面的鞋盒里讲话? 在某些夜晚,那门下透出的灯光驱走了我前行中的黑暗。
关于作者
安吉拉·普兰德利 (Angela?Pradelli,1959年出生),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也教授文学。参加过美欧等地的多项驻市活动,出版十余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以及与教育和语言有关的专著,多次获奖。
范文二:祖母的秘密
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百岁的从祖母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她闭着眼睛,安详地坐着,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与她的无声构成一幅安静的画面。那一刻,一百年的时光,凝固成一尊雕像。我轻轻地走过去,蹲下,靠近她。她睁开眼睛,混浊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接着,她又低下了头。然后又缓缓地抬起头来,她说我母亲的名字,但却忘记了我是母亲的大闺女还是小闺女。
她的双手紧紧地抱在衣衫的下面,像是躲避冷风的袭击,又像是在收藏某种重要的物品。这十几年来,她始终以这样的姿势坐着。在太阳下,在阴凉处,她无喜无忧地坐着。即使是唢呐的声音传来,她也从不过问是谁家的人去世了。仿佛这个世界的热闹或是安静都不会与她相关。她只是保持那样的姿势,一直坐着。到了吃饭的时间,她接过碗,少量地咽下几口饭,又回到她的姿势里。
这么多年,我从不曾见过她病了疼了的样子,她偶尔在深夜的时候,会莫名地呼唤着远嫁的女儿们的名字。第二天问她时,她又嫌弃问她话的人冤枉了她。她说,分明那是风吹过竹林的声音。竹林大片大片地生长在屋子的后面,每天晚上被风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从祖母彻夜地倾听着它们的语言,她知道它们的所有秘密。
多少次,我来来去去地经过她的面前,她呆滞地保持着同一表情,一动不动。我分不清她是看见我了,还是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而她众多的孙子们,自她保持这个姿势以来,她几乎是分不清楚他们的。只要他们不跟她说话,她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他们叫她时,他张冠李戴地叫着他们的名字,或是用含糊的声音问你是谁?问的次数多了,大家就把她当成了雕像。
这一次,我有些冒失地想要与她亲近些。我依偎着她坐下来,用手掰些糕点喂她吃。她用牙床上下左右地鼓动着,终于咽下去了。再要喂她,她摇头。我把手伸向她,她也高兴地伸出两只手,随即又赶紧缩回另一手。动作的迟缓,让她的秘密在阳光下暴露了。
几张卷缩着的百元大钞,在她的手心里被紧紧地揣着。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却不知该如何去补救。哪知,这个一直有些思维混沌的老人突然清醒地说话了。她说,这些都是亲戚给我的,我是用不上了,留着,也是你们的。然后她用另一只手去寻找旁边的拐杖,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而又要装做理直气壮的孩子。我知道她说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他的儿媳听的。
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90高龄过世。在她去世之前,对钱也是如此地重视过。她总是小心地用手帕把钱包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到哪带到哪。当上千元的钱丢失时又懊恼不已。尽管她哪里也去不了,但她一直保持着对钱财莫大的兴趣。某人给她钱物时,她会念叨人家的好处很久。她甚至在母亲不在家时,悄悄变卖些用不上的家什。但对于首饰,总是极度珍藏。她收藏饰品的地方很古怪,有时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有时又在沾满灰尘的瓦罐里。我的祖母,把那些东西当做她最大的秘密。
透过从祖母脸上的皱纹,我还看得出她年轻时美貌的痕迹。对于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从祖母,她的皱纹不是作家们描述的那种痛苦而深刻的意向,而是一种如丘陵般平和舒坦的细密曲线,沧桑中带着美丽。皱纹里既看不出痛苦,也见不到幸福。她像墙壁上挂着的一帧图片,而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像一部长长的小说。她的心里一定收藏着这个村庄最久远的秘密。只是,那些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它们远不如她手心里紧揣着的那几张钞票。
从祖父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一辈子也没下过田地。他戴着个黑边眼镜,两手背在身后,手里握着一本发黄的书,或是一把猪菜,目不斜视地从院子里走过。美人与书生的故事向来是故事中的精品。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是村庄里公开的秘密,被风传送得久远。
百年前的鲜活,在百年之后,注定只是一种传说。就比如从祖母手中紧握着的那几张钞票,其实它们现在的作用对于她而言仅只是几张废纸。从祖母之所以不愿意放手,是因为她一直想握住从前的岁月。曾经,她的生活是安定的,优裕的,甚至她可以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爱情,那种被书生称作是红袖添香的日子。在村庄里,这种意向必定可以代表一种高度,一种可以被别人羡慕的高度。
从祖父遗留下一本书,一本天书。发黄的扉页上写着一个久远的年代,书的材质是绵纸,就连装订的线是用绵纸捻成的线。他用洒脱劲道的笔力,描述着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姓氏的来历。我翻开它,犹如翻阅一个家族的秘密。我从我的父亲追溯回去,不知过了多少代以后,突然看到了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帝王的名字。若不是这样一种记载方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种事实的。且听人说这类事时的第一反应,总是有攀龙附凤之嫌。
这样的故事,从张家到李家,都有说法。难道,这散落的村庄里,都是些有来头的子民?不论多荣耀的过去,不论多辉煌的未来,经过一百年的沉淀。它们都成了泥土,成了大地的一部分。书上记载着的这些远祖的光环,到了今天,也就成了我的从祖母手中的那几张钞票,成了不是秘密的小秘密。看似贵重,实则也无多少实质的用处了。
向来,秘密只生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体现着某事对某人的重要性。村庄的秘密被记载在一本书里,我的祖母们的秘密都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许多秘密,在别的人眼里也许算不上是秘密,只因自己太在乎,所以成了秘密。人老了,最大秘密也许就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更或许是口袋里或手心握着的几张票子。在她们看来,身边存留着些钱财,就是给了自己安全的保证。安全,成了秘密的一把锁。我的祖母和从祖母都拼命地想锁住它。
责任编辑:赵 波
美术插图:黄耿辛
范文三:祖母的秘密
祖母的秘密
海夕家教
祖母的秘密
?原着/(美)佩特?艾甘?德克斯特 ?翻译/李明
我那13岁的孙女米歇尔肯定 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因为 当她来看我和她爷爷时,显得有些 焦躁不安,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想, 13岁对年轻女性的一生来说.这时 光是多么不可多得.看到孙女,我往 往也想起当年我13岁时的那个样 子.
我和米歇尔坐在一条长 午后,
椅上消磨时光.米歇尔穿着她那条 已退色的牛仔裤盘腿坐着,不停地 梳理她那浓密的深棕色头发.忽然1 间.米歇尔的脸上显出一阵不安的 神色.我不由得留神起来.米歇尔望I 着我说:"奶奶,恐怕七年级我得留 级了."
我的脸顿时红了,怎么,难道当 年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又落到 了米歇尔身上?当年,我也是在上七 年级时留了级,这可是我一生中最 为糟糕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一直严 守着这个秘密,心中一直为这件事
感到羞辱."我感到非常难受.妈妈 也伤心得很."米歇尔伤心地说. 我看到泪水从米歇尔那蓝色的 眼中涌了出来.她太好强了. 一
想到米歇尔正经受着我当年 经受过的同样的羞辱时,我感到十 分伤心.我耐心地给她以安抚,又朝 她身边挪了挪.双手握住她那温柔 的小手.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说: "当年,我的妈妈对我也是相当伤 心的."米歇尔惊讶地问:"奶奶.你 上学时也留过级?…'七年级时.米 歇尔."
我终于把严守多年的秘密泄露
当年这一 了.我紧接着告诉了孙女,
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我对老师是多 么生气,我也曾多么厌恶家庭作业 以及怎样不喜欢被别人命令做这干 那的.米歇尔仔细地听着我讲的每 一
个字.
"但最终,你还是毕业了,对
吧?"她问道."当然啦."我回过 神来又接着讲."我得赶快采取点 行动了.我要做个好梦,而且我还向 上帝作了祈祷.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首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 就是长大后做一名作家.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那时我决心好好努力.孩 子.这可是个好梦.后来.我真成了 一
名作家."
看来,米歇尔听了我的"秘密" 后.心情平静多了.她不声响地回到 了自己的房间.晚饭后.我又跟她坐 到了长椅上."奶奶,米歇尔和我 说道."您知道您说过一个梦.是 啊.我一直在想.我喜欢动物……" 我笑了.米歇尔在家里养的那 一
大群宠物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 的.
"我考虑了,我想做个兽医.奶 奶.那就是我的梦想吧.下次.我会 通过七年级的考试的——像你当年 做的那样."
我和孙女高兴地拥抱起来.米 歇尔不仅知道了我的秘密,而且和 我一样,在失败中学到了重要的一 课:一次失败不应当使我们感到羞 耻,只有当我们失败而不再尝试时,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羞耻. 图/邹勇编辑冯永平
?对孩子来说.往往一件在成人看来不经意的小事.也能影响他的一生.
范文四:祖母的秘密
祖母的秘密
苦瓜问卷 http://www.coolgua.com/kgwj/
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百岁的从祖母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她闭着眼睛,安详地坐着,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与她的无声构成一幅安静的画面。那一刻,一百年的时光,凝固成一尊雕像。我轻轻地走过去,蹲下,靠近她。她睁开眼睛,混浊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接着,她又低下了头。然后又缓缓地抬起头来,她说我母亲的名字,但却忘记了我是母亲的大闺女还是小闺女。
她的双手紧紧地抱在衣衫的下面,像是躲避冷风的袭击,又像是在收藏某种重要的物品。这十几年来,她始终以这样的姿势坐着。在太阳下,在阴凉处,她无喜无忧地坐着。即使是唢呐的声音传来,她也从不过问是谁家的人去世了。仿佛这个世界的热闹或是安静都不会与她相关。她只是保持那样的姿势,一直坐着。到了吃饭的时间,她接过碗,少量地咽下几口饭,又回到她的姿势里。
这么多年,我从不曾见过她病了疼了的样子,她偶尔在深夜的时候,会莫名地呼唤着远嫁的女儿们的名字。第二天问她时,她又嫌弃问她话的人冤枉了她。她说,分明那是风吹过竹林的声音。竹林大片大片地生长在屋子的后面,每天晚上被风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从祖母彻夜地倾听着它们的语言,她知道它们的所有秘密。
多少次,我来来去去地经过她的面前,她呆滞地保持着同一表情,一动不动。我分不清她是看见我了,还是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而她众多的孙子们,自她保持这个姿势以来,她几乎是分不清楚他们的。只要他们不跟她说话,她从不主动开口说
话。他们叫她时,他张冠李戴地叫着他们的名字,或是用含糊的声音问你是谁,问的次数多了,大家就把她当成了雕像。
这一次,我有些冒失地想要与她亲近些。我依偎着她坐下来,用手掰些糕点喂她吃。她用牙床上下左右地鼓动着,终于咽下去了。再要喂她,她摇头。我把手伸向她,她也高兴地伸出两只手,随即又赶紧缩回另一手。动作的迟缓,让她的秘密在阳光下暴露了。
几张卷缩着的百元大钞,在她的手心里被紧紧地揣着。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却不知该如何去补救。哪知,这个一直有些思维混沌的老人突然清醒地说话了。她说,这些都是亲戚给我的,我是用不上了,留着,也是你们的。然后她用另一只手去寻找旁边的拐杖,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而又要装做理直气壮的孩子。我知道她说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他的儿媳听的。
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90高龄过世。在她去世之前,对钱也是如此地重视过。她总是小心地用手帕把钱包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到哪带到哪。当上千元的钱丢失时又懊恼不已。尽管她哪里也去不了,但她一直保持着对钱财莫大的兴趣。某人给她钱物时,她会念叨人家的好处很久。她甚至在母亲不在家时,悄悄变卖些用不上的家什。但对于首饰,总是极度珍藏。她收藏饰品的地方很古怪,有时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有时又在沾满灰尘的瓦罐里。我的祖母,把那些东西当做她最大的秘密。
透过从祖母脸上的皱纹,我还看得出她年轻时美貌的痕迹。对于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从祖母,她的皱纹不是作家们描述的那种痛苦而深刻的意向,而是一种如丘陵般平和舒坦的细密曲线,沧桑中带着美丽。皱纹里既看不出痛苦,也见不到幸福。她像墙壁上挂着的一帧图片,而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像一部长长的小说。她的心里一定收藏着这个村庄最久远的秘密。只是,那些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它们远不如她手心里紧揣着的那几张钞票。
从祖父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一辈子也没下过田地。他戴着个黑边眼镜,两手背在身后,手里握着一本发黄的书,或是一把猪菜,目不斜视地从院子里走过。美人与书生的故事向来是故事中的精品。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是村庄里公开的秘密,被风传送得久远。
百年前的鲜活,在百年之后,注定只是一种传说。就比如从祖母手中紧握着的那几张钞票,其实它们现在的作用对于她而言仅只是几张废纸。从祖母之所以不愿意放手,是因为她一直想握住从前的岁月。曾经,她的生活是安定的,优裕的,甚至她可以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爱情,那种被书生称作是红袖添香的日子。在村庄里,这种意向必定可以代表一种高度,一种可以被别人羡慕的高度。
从祖父遗留下一本书,一本天书。发黄的扉页上写着一个久远的年代,书的材质是绵纸,就连装订的线是用绵纸捻成的线。他用洒脱劲道的笔力,描述着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姓氏的来历。我翻开它,犹如翻阅一个家族的秘密。我从我的父亲追溯回去,不知过了多少代以后,突然看到了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帝王的名字。若不是这样一种记载方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种事实的。且听人说这类事时的第一反应,总是有攀龙附凤之嫌。
这样的故事,从张家到李家,都有说法。难道,这散落的村庄里,都是些有来头的子民,不论多荣耀的过去,不论多辉煌的未来,经过一百年的沉淀。它们都成了泥土,成了大地的一部分。书上记载着的这些远祖的光环,到了今天,也就成了我的从祖母手中的那几张钞票,成了不是秘密的小秘密。看似贵重,实则也无多少实质的用处了。
向来,秘密只生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体现着某事对某人的重要性。村庄的秘密被记载在一本书里,我的祖母们的秘密都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许多秘密,在别的人眼里也许算不上是秘密,只因自己太在乎,所以成了秘密。人老了,最大秘密也许就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更或许是口袋里或手心握着的几张票
子。在她们看来,身边存留着些钱财,就是给了自己安全的保证。安全,成了秘密的一把锁。我的祖母和从祖母都拼命地想锁住它。
责任
美术插图:黄耿辛
苦瓜问卷
范文五:.祖母的秘密
秸杆利用 http://www.tixmny.net
2014年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与林老接触的点点滴滴
或者永恒 刹那,
一只鸟瞄准一座村庄
忆我父母的爱
妈,我还想吃您做的饭
过冬天这条河
前门飘香桂花树
雪夜中的背影
人人梦里有一片海
秋高气爽蘑菇香
会吃的靖江人
中国人的习惯
金刀劈开的峡谷
在德天瀑布前
笑是一剂良药
秦椒和陕西面食
秸杆利用 http://www.tixmny.net
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百岁的从祖母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她闭着眼睛,安详地坐着,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与她的无声构成一幅安静的画面。那一刻,一百年的时光,凝固成一尊雕像。我轻轻地走过去,蹲下,靠近她。她睁开眼睛,混浊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接着,她又低下了头。然后又缓缓地抬起头来,她说我母亲的名字,但却忘记了我是母亲的大闺女还是小闺女。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6686499.htm
她的双手紧紧地抱在衣衫的下面,像是躲避冷风的袭击,又像是在收藏某种重要的物品。这十几年来,她始终以这样的姿势坐着。在太阳下,在阴凉处,她无喜无忧地坐着。即使是唢呐的声音传来,她也从不过问是谁家的人去世了。仿佛这个世界的热闹或是安静都不会与她相关。她只是保持那样的姿势,一直坐着。到了吃饭的时间,她接过碗,少量地咽下几口饭,又回到她的姿势里。
这么多年,我从不曾见过她病了疼了的样子,她偶尔在深夜的时候,会莫名地呼唤着远嫁的女儿们的名字。第二天问她时,她又嫌弃问她话的人冤枉了她。她说,分明那是风吹过竹林的声音。竹林大片大片地生长在屋子的后面,每天晚上被风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从祖母彻夜地倾听着它们的语言,她知道它们的所有秘密。
多少次,我来来去去地经过她的面前,她呆滞地保持着同一表情,一动不动。我分不清她是看见我了,还是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而她众多的孙子们,自她保持这个姿势以来,她几乎是分不清楚他们的。只要他们不跟她说话,她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他们叫她时,他张冠李戴地叫着他们的名字,或是用含糊的声音问你是谁,问的次数多了,大家就把她当成了雕像。
这一次,我有些冒失地想要与她亲近些。我依偎着她坐下来,用手掰些糕点喂她吃。她用牙床上下左右地鼓动着,终于咽下去了。再要喂她,她摇头。我把手伸向她,她也高兴地伸出两只手,随即又赶紧缩回另一手。动作的迟缓,让她的秘密在阳光下暴露了。
几张卷缩着的百元大钞,在她的手心里被紧紧地揣着。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却不知该如何去补救。哪知,这个一直有些思维混沌的老人突然清醒地说话了。她说,这些都是亲戚给我的,我是用不上了,留着,也是你们的。然后她用另一只手去寻找旁边的拐杖,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而又要装做理直气壮的孩子。我知道她说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他的儿媳听的。
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90高龄过世。在她去世之前,对钱也是如此地重视过。她总是小心地用手帕把钱包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到哪带到哪。当上千元的钱丢失时又懊恼不已。尽管她哪里也去不了,但她一直保持着对钱财莫大的兴趣。某人给她钱物时,她会念叨人家的好处很久。她甚至在母亲不在家时,悄悄变卖些用不上的家什。但对于首饰,总是极度珍藏。她收藏饰品的地方很古怪,有时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有时又在沾满灰尘的瓦罐里。我的祖母,把那些东西当做她最大的秘密。
透过从祖母脸上的皱纹,我还看得出她年轻时美貌的痕迹。对于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从祖母,她的皱纹不是作家们描述的那种痛苦而深刻的意向,而是一种如丘陵般平和舒坦的细密曲线,沧桑中带着美丽。皱纹里既看不出痛苦,也见不到幸福。她像墙壁上挂着的一帧图片,而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像一部长长的小说。她的心里一定收藏着这个村庄最久远的秘
秸杆利用 http://www.tixmny.net 密。只是,那些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它们远不如她手心里紧揣着的那几张钞票。
从祖父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一辈子也没下过田地。他戴着个黑边眼镜,两手背在身后,手里握着一本发黄的书,或是一把猪菜,目不斜视地从院子里走过。美人与书生的故事向来是故事中的精品。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是村庄里公开的秘密,被风传送得久远。
百年前的鲜活,在百年之后,注定只是一种传说。就比如从祖母手中紧握着的那几张钞票,其实它们现在的作用对于她而言仅只是几张废纸。从祖母之所以不愿意放手,是因为她一直想握住从前的岁月。曾经,她的生活是安定的,优裕的,甚至她可以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爱情,那种被书生称作是红袖添香的日子。在村庄里,这种意向必定可以代表一种高度,一种可以被别人羡慕的高度。
从祖父遗留下一本书,一本天书。发黄的扉页上写着一个久远的年代,书的材质是绵纸,就连装订的线是用绵纸捻成的线。他用洒脱劲道的笔力,描述着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姓氏的来历。我翻开它,犹如翻阅一个家族的秘密。我从我的父亲追溯回去,不知过了多少代以后,突然看到了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帝王的名字。若不是这样一种记载方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种事实的。且听人说这类事时的第一反应,总是有攀龙附凤之嫌。
这样的故事,从张家到李家,都有说法。难道,这散落的村庄里,都是些有来头的子民,不论多荣耀的过去,不论多辉煌的未来,经过一百年的沉淀。它们都成了泥土,成了大地的一部分。书上记载着的这些远祖的光环,到了今天,也就成了我的从祖母手中的那几张钞票,成了不是秘密的小秘密。看似贵重,实则也无多少实质的用处了。
向来,秘密只生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体现着某事对某人的重要性。村庄的秘密被记载在一本书里,我的祖母们的秘密都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许多秘密,在别的人眼里也许算不上是秘密,只因自己太在乎,所以成了秘密。人老了,最大秘密也许就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更或许是口袋里或手心握着的几张票子。在她们看来,身边存留着些钱财,就是给了自己安全的保证。安全,成了秘密的一把锁。我的祖母和从祖母都拼命地想锁住它。
责任编辑:赵 波
美术插图:黄耿辛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http://www.xzbu.com/5/view-6686499.htm
秸杆利用 http://www.tixmn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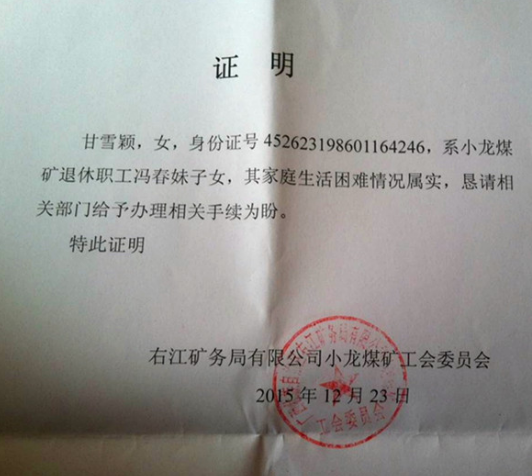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Lk_颜良
Lk_颜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