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一:东亚奇迹与人口
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
王德文
【中文摘要】本文总结了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人口转变带来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东亚经济带来了一次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本和“四小龙”抓住机遇,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人力资源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既收获了人口红利,又推动了经济起飞。不过,随着人口老化,日本的现收现付制度对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冲击。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养老制度安排,对收获人口红利和化解人口负债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经济增长、东亚奇迹
【作 者】王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曾先后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和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询它背后的故事。
在对“东亚奇迹”的众多研究中,人口转变因素逐步受到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充分重视,被誉为是“东亚奇迹”背后的重要变量和决定性因素之一。确实,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关闭,人口老龄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同程度冲击。本文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希望为中国处理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东亚的经济发展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1913年到195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只有2.21%;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为9.29%;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Maddison ,2001)。日本人均收入也显示了相同的增长态势(见表1)。在6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长强劲,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4%。70年代之后,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在90年代经济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在2%以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而且还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率。
表 1 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增长:1960-2004
1960-1970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全球平均 1970-19801980-19901990-2000 2000-20049.34 3.89 3.25 1.53 1.48 5.65 5.47 6.52 5.46 4.73 7.37 7.70 5.25 4.76 2.34 7.11 6.94 5.52 2.85 4.04 6.02 7.84 6.43 5.30 2.83 4.11 2.64 2.21 1.90 1.70 3.16 3.60 1.34 2.07 3.76 1.72 1.01 1.97 2.22 3.24 3.24 1.87 1.25 1.36 1.62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从60年代初开始,时间上比日本晚十年左右。从1960年到2000年,“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在5.6%-6.4%之间(见表1)。在这四十年时间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香港人均收入在6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保持在7.11%。新加坡和台湾人均收入都是在7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接近8%。韩国人均收入在8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6.52%。经过大约40年的经济增长,“四小龙”相继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经济的行列。不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四小龙”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图1 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1960-2004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以美国人均收入水平
为参照对象,图1显示了1960年到2004年日本和“四小龙”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 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 水平的50.2%、7.9%、15.6%、
21.4%和7.2%。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 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 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
东亚经济增长不仅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
人类社会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了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都有明显进步。
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等众多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总体福利状况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越大,说明它的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越好。
表 2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
年份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 日本 0.857 0.882 0.895 0.911 0.925 0.936 0.943 韩国 0.707 0.741 0.78 0.818 0.855 0.884 0.901 新加坡 0.725 0.761 0.784 0.822 0.861 - 0.916 香港 0.761 0.800 0.827 0.862 0.882 - 0.916 美国 0.867 0.887 0.901 0.916 0.929 0.938 0.944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USA.
表2列举了1975年到2005年日本、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1975年,日本的经济起飞已经完成,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伴随着经济增长,日本的社会事业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75年,日本人类发展指数为0.857,与美国人类发展指数非常接近。此后,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上表现出相似的上升速度。同样,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也有显著提高。从1975年到2003年,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提高了0.194、0.191和0.155,均高于同期日本和美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上升速度。通过成功的经济追赶,日本和“四小龙”与美国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趋同化的态势。
二、什么创造了“东亚奇迹”?
在Solow (1956)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物质资本增长由外生的利率变量决定,劳动力数量增长由外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决定,因此,物质资本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在长期都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当经济增长过渡到稳态均衡之后,人均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这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
如果把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那么,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后来,内生增长模型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归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也是由人力资本回报的外生变量决定,那么,扣除人力资本之后的剩余部分,即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唯一因素。
经济学家之间对“东亚奇迹”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Young (1994)认为,所谓“东亚
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从1966年到1990年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要素积累。在此期间,“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随着部门间劳动力重新配置,非农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
1.5-2倍。在25年中,“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3%-4%。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OECD 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
Krugman (1994)认为,神话般的亚洲奇迹只不过来自高投入的经济增长。这种神话与前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相似。前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推动了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是当时美国经济的3倍。当时,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虽然批评前苏联经济数据有夸大成份,但也承认其增长的事实。美国经济学家凯尔文·胡佛甚至得出“一个集体主义的独裁式政府在本质上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式政府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他还预测前苏联经济将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超过美国。Krugman 用前苏联作为例子类比,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他还进一步将“四小龙”与日本做比较。他认为,日本在技术创新上接近美国,技术进步在日本经济增长中有很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四小龙”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种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Bhagwati (1996)不同意Krugman 的看法。他认为,
实。“四小龙”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投资率都非常高,并持续了20-30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Krugman 认为“四小龙”没有技术进步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追赶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如果把东亚经济增长按照每1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进步上是递增的。同时,Krugman 对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Desai (1990)研究,缺乏有效激励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是前苏联计划经济走向崩溃的原因,而不是来自边际报酬递减所带来的投资下降。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因素,它所带来的出口增长、国际竞争、FDI 流入、人力资源开发等因素,不仅刺激了国内投资,而且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World Bank(1993)从1991年到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能够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经济获得成功没有任何“奇迹”而言。但是,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于它们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充分开发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东亚奇迹的实质是不仅有高速增长,而且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东亚奇迹”中的人口因素
无独有偶,东亚经济起飞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
。这种积极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带来了丰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迅速转变阶段(见表3)
裕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了储蓄率,增加国内资本供给。因此,人口转变在特定阶段将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
表3 1947-2004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口增长率(‰)
日本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韩国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台湾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1947 34.3 14.6 19.7 38.3 18.2 20.2
43.3 11.5 31.8 1950 28.1 10.9 17.2 37.0 16.9 20.1
1955 19.4 7.8 11.6 45.7 14.9 30.8
1960 17.2 7.6 9.6 39.6 12.5 27.1
1965 18.6 7.1 11.5 33.0 10.4 22.6 45.3 8.6 36.7 39.6 7.0 32.6 32.7 5.5 27.3 1970 18.8 6.9 11.9 31.2 8.0 23.2 27.2 4.9 22.3 1975 17.1 6.3 10.8 24.8 7.7 17.1 23.0 4.7 18.3 1980 13.6 6.2 7.4 22.7 7.3 15.4 23.4 4.8 18.6 1985 11.9 6.3 5.6 16.2 6.0 10.2 18.0 4.8 13.2 1990 10.0 6.7 3.3 15.4 5.8 9.6 16.6 5.2 11.3 1995 9.6 7.4 2.1 16.0 5.4 10.6 15.5 5.6 9.9 2000 9.5 7.7 1.8 13.4 5.2 8.2 13.8 5.7 8.1 2004 8.8 8.2 0.6 9.8 5.1 4.7 9.6 6.0 3.6
资料来源:Na tiona 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Japan (2003)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es and Communications of Japan,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6, ;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台闽地区人口统计》(历年)。 Database, ; 台湾内政部,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在早期,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如果人口出生率一直较高,那么,快速的幼年人口成长,将会带来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人口负担不断加重。随着生育转型加快,出生率下降带来幼年人口成长压力减少,而先前快速成长的幼年人口已经成为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于是带来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此后,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老年抚养比上升推动着总抚养比不断上升,回到高抚养比的人口负担水平。因此,人口转变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期。《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World Bank, 2002)。
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亚经济由过一(Mason, 1997;Bloom and Williamson,1997)
去的人口负债阶段过渡到人口红利阶段,这个过程到其结束大约有50年左右的时间。一般而言,东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2.6%。但是,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估算,东亚经济在1966-1990年人均GDP6-7%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大约有1.4-1.9个百分点,也就是讲,相当于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的1/3(Bloom and Williamson,1997)。
图2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抚养比变化:1950-2050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05-11-14.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 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人力规划处,《台湾民国93年至140年人口推计》(2004)。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口因素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老龄化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出生率迅速下降意味着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总抚养比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进入了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时期(见图2)。二是日本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三是教育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国民素质,使日本在一代人的成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当时,日本通过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大企业通过终审雇佣制度和培训制度,培养和留住企业所需的特定人才。在农村,通过建立众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等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使农村劳动力获得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些措施,一方面满足了日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训练有素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源积累实现科技创新,推动了技术进步。
亚洲“四小龙”的相似发展经验,也证明了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关联。1961年,韩国把家庭计划确立为一项国策,并把人口控制目标规划纳入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家庭计划政策实施,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带来了总抚养比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1995年的41.4%,从而开启了韩国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见图2)。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时间里,将人均GDP 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跃升至1995年的1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我国台湾省的人口转变时间和经济起飞时间比韩国稍早,但比日本稍晚。台湾人口抚养比呈现两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张喻婷、陈信木,2005)。在1950年到1965年期间,幼年抚养人口数量快速扩张带来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在1962年达到最高点的94.1%。1960年代中期之后,人口抚养比的压力减缓,抚养比在1995年下降到45.8%。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在人口转变的同时,台湾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如从60年代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服务。这些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也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东亚奇迹”中的政府角色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一次性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经济发展将有可能失去实现起飞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会为人口负债背上沉重负担。能否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政策措施。总体而言,日本和“四小龙”都是通过制定和运用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
图3 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度:1960-2004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 台湾行政院,《国民所得统计》(历年)。
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日本和“四小龙”的起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 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 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相比日本,“四小龙”出口导向特征非常显著。从图3可见,伴随经济起飞,韩国对外贸易占GDP 比重从不到20%上升到60%以上,台湾对外贸易占GDP 比重从不到25%上升到80%以上,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 的1-3倍。
出口导向战略在本质上是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这种战略将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年到1975年期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台湾在1970年代的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年到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
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图4 东亚经济的劳均资本数量积累:1965-1991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负担下降和外直接投资(FDI )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了国内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了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Leff ,1969;Mason ,1997)。日本在1960年到1975年期间,国民储蓄率平均在36.2%。从1965年到1995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打破了低水平的发展陷阱,踏上经济成长的快车道。图4展示了1965年到1995年期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五、东亚人口转变前景及其影响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总和生育率急速下降,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整
劳动供给短缺诱发的劳动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因素之一。由于各自个社会迅速老化,
的人口转变起点时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体制和政策、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它们所获人口红利的时间终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四小龙”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而日本收获人口红利阶段已经结束,需要担负起老龄化社会的养老负担。
图5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2005-2050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05-11-14.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目前,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195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只有4.9%。伴随着经济起飞,日本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只用了20年时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年,老龄化率上升到7.1%。目前,日本老龄化率接近20%,相当于每五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从趋势上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将进一步老化。到2020年,大约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到2040年,大约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见图5)。亚洲“四小龙”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结果带来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更快。到2050年,韩国和台湾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接近甚至超过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例如,日本的人口负担系数在1970年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之后,人口负担系数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给日本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人口老化所支付的社会负担急剧上升。人口结构老化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首先,人口老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抚养比,减少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这相当于增加了对他们的收入税,因此,削弱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意愿,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数量。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Pench (2000)认为,老年抚养比只是一个人口学定义,它没有考虑真正提供收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是老年经济抚养比,它是指被抚养老年人口数量相当于所有就业人口的比例。如果考虑经济抚养比,那么,人口老龄化状况则更加严重。例如,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则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影响大约在0.5个百分点。
其次,现收现付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私人储蓄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同时,人口结构老化之后,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据测算,从1970年到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Yamada and Yamada ,1988)。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这种危机进一步诱发了经济增长问题。
最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Hewitt (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日本劳动力市场非常僵硬(如终生雇佣制度),技术创新不足,储蓄减少和劳动供给下降,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资本市场不健全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的,人口老龄化是这些问题的内在诱因,“旧思维和旧行为的老化日本,是日本政治危机的症结。”日本能否渡过这个危机,关键看日本如何改革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为日本经济摆脱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结论
在传统的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经济学中,人口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代名词,人口数量增长结果会带来食品消费短缺问题和环境资源压力问题。所谓环境资源压力只不过是食品消费短缺问题的现代翻版。这种绝对的人口数量观不仅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且以忽略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制约。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可以把人口从简单的消费者转变为同时也是生产者,激发人类发明创造的潜能,推动技术进步,从而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在人口、自然和环境之间形成和谐关系。
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我们树立新的人口观提供了一个现实支撑。然而,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并不是天赐禀赋,可以自动地获取。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是一次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经济起飞,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促进市场发展和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收获人口红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有人口红利期,就会有人口负债期。当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快,而“四小龙”的未来老龄化速度比日本还快。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帐户危机和财政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有惊人的相似性(黑田俊夫,1993)。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蔡昉,2004;王德文等,2004)。然而,无论是从收入水平还是从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都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一是通过最大化地实现充分就业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十一五”期间,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处于劳动力供给高峰。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而且也是发掘人口红利的唯一途径。二是建立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养老保障水平相差悬殊。即使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翻两番”
的目标,届时人均收入水平大约在3000美元左右,但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在这样收入水平上,现收现付制不可能为全民提供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积累制度是一个可行而现实的选择。三是加大对教育、培训、卫生健康等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以及对科学研究和研发等方面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克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参考文献:
1. 蔡昉(2004):《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2期,第2-9页。
2. 黑田俊夫(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第4期。
3. 台湾行政院:《国民所得统计》(历年);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人力规划处:《台湾民国93年至140年人口推计》(2004);台湾内政部:《台闽地区人口统计》(历年)。
4.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第5期,第2-11页。
5. 张喻婷、陈信木(2005):《台湾地区人口视窗分析》,台湾人口学会学术研讨会“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口发展:趋势与挑战”会议论文,台北。
6. Andrew Mason (1997), 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 East-West Center, 1997, Honolulu, Hawaii.
7. Angus Mad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 OECD.
8. Bloom, David and Jeffrey Williamson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68.
9. Jagdish Bhagwati (1996), 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on May 3, 1996 at Cornell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Performance to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10. Krugman, Paul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4.
11. Leff, Nathaniel H. (1969),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olume 59(5): 886~896.
12. Lucio Pench (2000),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raying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 A Policy Conference on Global Aging, January 25-26, 2000, Washington.
13.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Japan (2003).
14.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es and Communications of Japan,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6, .
15.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
16. Padam Desai (1990), The Soviet Econom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aperback edition.
17. Paul S. Hewitt (2003), The Gray Roots of Japan’s Crisis,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No.10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8.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0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 2005-11-14.
19.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2(1): 65~94.
20. Tetsuji Yamada and T. Yamada (1988), The Effects of Japanes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Benefits on Personal Savings and Elderly Labor Force Behavi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2661.
2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York, 10017, USA.
22.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3.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 , Washington D.C., New York.
24. 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
25. Young, Alwyn (1994),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4680.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ast Asian Miracle: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Dewen W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 to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The productiv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resulting from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window” for East Asian economy to harvest demographic dividend. Japan, Hong Kong, Taiwan, Singapore and Korea firmly grasped this opportunity and realized their economic takeoff through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utilization. However,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wake of their economic takeoff produced shocks on their economic growth. Th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in those econom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arrangement of old age support system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gai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relief of demographic debt.
Key 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Demographic Debt, Economic Growth and East Asian Miracle
范文二:东亚经济奇迹
东亚经济奇迹
东亚发展模型
透过政府干预而增长的“日本模型”亦不能应用在东亚发展国家中,原因是套用在发展中东亚
国的模型,至少已有,个。
香港及新加坡
虽然两个城市与其他增长迅速的岛屿,尤其马尔他甚为相似,但两者在区内可算是各自精彩。纵使他们在,,年代末期已是地位巩固的转口港,但贸易方向截然不同。有趣的是,这点奠定两个城市走向不同经济发展方向的相异处往往倍受忽视。香港向中国输入原材料,而从中国输出劳动密集制成品。,,年代末期,众多中国企业家逃往香港及台湾,其中主要来自上海的能带机械逃难。部分企业家甚至向保险索偿机械器材的损失,以获得营运资金。他们迅速地发展及扩展其出口业务,专营塑胶花、成衣、纺织、玩具、运动用品及其他劳动密集货品。香港的英国殖国地政府提供了中立的经济环境:低盈利进口关税(,(,,)带来宏观经济的稳定局面、低统一公司及个人收税(原先,,(,,,上升至,,(,,),及主要来自流动盈利,为原先少于,,,万,后增长至,,,万的人口,迅速建立了社会及物质的基础。由于经济规模少及开放,货币政策的工具无异较弱。移民控制如劳工政策,因而亦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
由于缺乏农业,香港以最高的价钱输入食品,而将其他廉价消费品及输入品输出亦紧随而来。要是考虑欠周的国家有意将廉价货物在香港倾销,香港消费者及制造商会非常高兴。
低通胀及不断增长的出口,鼓励人民储蓄及投资。此外,对海外投资的开放态度亦有利于极具支持性的经济环境。虽然输出口制造起初以本地为主,但香港后期吸引海外企业,利用香港劳动人口生产劳动密集货品出口。这有助香港通向全球市场及全球科技“架”。只要没有为出口商提供保护或“赠送”奖励,如免税期,海外投资者剥削经济的危险便不会出现。
政府管制大都受制于土地计划。计划目的是令香港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屿及其邻近地区适合居住。虽然取缔潜建楼宇交由私人户主拥有,但公共投资仍包括公共房屋。
大批移民流入引发激烈的斗争并激化了灵活性。正如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吸纳大量员工的并非工厂,而是涉及经济范围的“非正式”行业。分包合同透过非正式及正式聘请来加强劳工使用率。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劳动人口的技术及其工资亦大大提高,每年实质增长有,,,,而正迅速增长的在职家庭收入亦上升。香港经济亦因为旅游业而变得多元化,而金融服务、大规模传统贸易行业及不断增长的制造出口,对香港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有来自中国的各类型制造品出口的中间人服务扩张,情况自,,,,年中国开放政策实施后更有上升趋势。而香港制造业亦变得非常成熟。
随着资金上升,香港企业家着手投资海外,以便利用其管理及市场经济来扩充生产。直至,,年代末期,这些企业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的出口工业,已成为重要投资者。
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厂家便纷纷将非技术性的劳动密集运作迁往大陆。估计香港企业家目前在中国雇用的员工人数至少有,,,万人,单在珠江三角洲已有,,,万人。他们主要负责出口制造,人数远远超过香港总劳动人口。虽然中国生产人数较香港的多出,,,万,但香港的制造出口接近,,,亿美元,而中国则只有,,,亿。由于香港主要集中较高技术生产过程,所以以每一元计,香港的增值额较中国高。
新加坡与香港刚好相反,属向内为主的转口港,为马来西亚、印尼及泰国从其他地方输入制成品,及负责将其基本产品,主要是锡、椰油及树胶、进行分类、包装及分工,然后再输出国外。
新加坡自,,年代末期取得独立后,由于得到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机构支持,遂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向内为主制造中心。这正好配合李光耀新社会主义政府的意识形态。他希望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农业腹地的工业中心。新加坡政府透过直接投资及“挑选赢家”(保护联邦市场输入代替品),从而在制造业担当重要角色。然而,基于联邦的种族组合,尤其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李光耀的展望
未能实践。新加坡于,,,,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迅即发现自己须面对多重严峻打击。首先,英国有意撤回军队,而英国驻军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主要经济资源。另外,由于联邦逐渐变得自我保护,新加坡亦继而失去马来西亚这个市场。与此同时,印尼提出对抗政策,试图从新加坡手中取回印尼输出口的中间人角色。
,,,,年,新加坡人的资金,继日本之后是全亚洲最高,但失业率至少有,,,。由马克思
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行动激进,造成工业关系非常恶劣。于是政府向工会游说,要经济繁荣、就业率增长及资金上升,工会行动得理性化。此外,正式工会行业以外的工人利益亦须受到关注。
一夜之间,新加坡由向内出口转为向外出口。这种急剧的转变可在新加坡发生,原因是她在马来西亚两年期间,所行的保护主义道路不是太远。有别于香港,新加坡没有向海外销售劳动密集制成品的经验。因此,新加坡邀请世界各地,尤其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使用其劳动人口及基础设施作为出口基地,新加坡能成功吸引国际企业,在于她能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及保健),一个个全球竞争性及高效率的实质基础设施(交通及电子通讯),以及一个廉洁的政府。此外,新加坡亦提供高级住宅,起初只限于公营部门,但后来仍售与私人拥有。这对经济生产力及政治稳定有莫大贡献。
仅仅,年后,即,,,,年,新加坡的制成品出口及经济突飞猛进。直至,,年代,新加坡出现劳工短缺,所以从马亚西亚、菲律宾及其他邻近国家输人,,,,,,,,,,,,。由于贸易持续增长,新加坡大有机会成为全球第二大港口(首位是纽约)。与此同时,新加坡旅游业昌盛、金融业亦在发展当中。
香港方面,低通胀及稳定汇率鼓励高储蓄及投资。作为刺激私人屋宇及退休储蓄的公积金,为公共投资提供资源。经济开放再次限制货币工具的使用。
当实质资金上升,制造业及其他行业更趋复杂化。在不足,,年间,由电子零件的简单装配,转移到零件制造的精密工程,以至“机械人”生产。新“三角”政策现已实行,目的是在马来西亚及印尼,从那些对新加坡已没有经济效率的工业,聘用相对没有技能的廉价劳工。到,,年代末期,单在印刷副产品工业工作的员工有,,万人。新加坡有超过七成的制造出口由外国企业生产。正如香港一样,由于没有保护政策,及为数甚少的本土管制,再加上销售地点主要以世界市场为主,外国企业难以在新加坡取得垄断地位,有异于香港殖民地政府。新加坡政府自,,,,年宣布独立后,有着浓烈的干涉主义味道。生产公共投资由向内及干涉主义政策衍生。新加坡亦成立经济发展局,目的是以一个“一站店”的模式处理迅速的市场流入,尤其协助对经济甚为重要的外国投资者进驻本地市场。新加坡政府仍采用由马亚西亚联邦规例制定的免税期。及为外国公司提供保护主义环境、信贷及土地资助。而这些已成为经济发展局官员与外国投资者磋商的主要“卖点”。但与会的投资者指出,这些好处对他们作投资决策没有太大影响,这亦证实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新加坡试图“挑选赢家”的政策有碍生产,所以不久便遭抛弃。而由官方“挑选”的首个出口工业,成衣及纺织,亦彻底失败,成衣出口从未“出口”,相反电子装配却兴盛起来。而获得丰厚资助的“新加坡丝”亦告失败,最后亦被放弃。自从一间享负盛名的照相机企业,在新加坡取得垄断地位后倒闭,剥夺新加坡发展镜片科技机会后,新加坡已对“挑选赢家”失去信心。由于新加坡官员有意维持管理环境,有关的讨论仍持续不断。但新加坡政府为了顺从市场走势,特别是要争取爬上技术及科技阶梯的机会,也决定放弃选赢家政策。
经过,,年非常成功的发展,新加坡政府明白,他们大部分的干预要不是有碍生产,便是多余,所以正着手撤消参与商业生产,及考虑进一步私有化,甚至包括“公共货品”。收入税收亦相对高(对企业征收接近,,,,要是再加上公积金供款,个人的征税还要高)。政府亦有意取消征税优惠以支持低企业税,务求提高效率。信贷资助到,,年代已大大削减。有人认为减少公共干预可让众多有为的政府官员投身商界,更能让他们发挥所长。
新加坡政府透过空间计划,对经济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的主要贡献,更甚于香港政府。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在没有付出任何经济成本下,注重环境建设及自然美。在城市运输政策方面,新加坡处于全球领导地位。大众公共交通完善。纵使人民拥有汽车比率高,但交通挤塞情况绝
无仅有。价格往往与宽松管制共同使用,以达到社会美满。
台湾及韩国
两国经济的“初步情况”颇具分别。台湾在,,年代的农业经济发展颇为不俗,亦没有受到二次大战太大影响,到,,年代末期,更有大批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及企业家流入。正如香港情况一样,这些新移民大都拥有资金、机械及世界市场知识。相反,韩国则饱受内战摧残。,,年代早期,韩国非常贫穷,人均收入比菲律宾还要低。到冬天,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寒交迫下死去。两国亦曾因为殖民地主及其封建合作者剥夺他们土地拥有权,而进行多次土地改革,但至,,年代,由于向内及保护主义政策,亦导致农业停滞不前。财政问题亦紧随保护主义出现。而两国在严重的财政大萧条的打击下,须寻求避难所。利率须维持低水平,而借贷则经由政府推出,再配给大型企业。,,年代的大笔资助不是被贪官污吏花掉,便是往海外汇款甚至遭浪费。当时通胀过高、汇率过高、经济不景气亦随之而来。但令人惊叹的是,该段期间的教育经费及对初步工业的保护,正奠定日后工业出口的基础。两国的贸易进步都须与政策偏见对衡。
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台湾终在,,年代末期开始发展,而韩国则在,,年代初期开始。其实,加速两国发展的元素,是由于美国减少甚至撤消对他们的庞大非军事援助。两国随即改革财政政策,及致力平衡预算案,基础设施亦在此架构下展开。货币政策须在没有严重削弱经济情况下收紧,通胀亦已得到控制,而汇率亦须降低以平衡供款均衡水平及维持经济稳定。
无论在台湾或韩国,改革者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推翻保护主义,或引入具竞争性的财政体系。因此,它们须尝试透过撤销农业及出口的保护政策及利用贷款配给来达到“中立”。
对抗保护主义政策的方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不会带来副作用,让出口商透过人口限制及人口税的豁免,以全球价格输入原料。其他好处包括对农业原料的资助、提供通往本地市场的专有渠道(透过专营及进军市场限制)。“浪费津贴”、资助贷款及免税期能否刺激出口不但已受到质疑,而且有损经济,负责的行政队伍往往都是些想法主观、行事有碍生产的人。
要解决保护主义及对抗干预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代价沉重。财政“萧条”歪曲了行内及行业间的投资。推行周详的减轻农村贫穷计划旨在减低人们对农业的偏见所造成的影响。大规模直接干预制造及服务工业是必须的,务求舒缓为不同生产成本而设的“特定”关税带来的影响。这大大有利大型企业及员工。
“非正式”的劳动人口须承受保护主义,以及因对抗保护主义而起的干预及津贴所衍生的代价。歪曲政策制造政府财政及宏观经济成本,削弱了社会及环境基金的供应。房屋及其他社会福利设施方面都落在香港及新加坡后面。当台湾及韩国的人均收入上升,他们的保护主义连同补助政策被视为是对抗关税及贸易税协定(,,,,)。贸易报复问题一触即发。
韩国在,,年代末期以及,,年代末期,恢复公共投资,及资助私营企业投资“基本”工业。居所工业保护主义意识形态是部分推动力,但策略考虑亦是主要元素。韩国曾试图建设金属加工、重型工程及化学工业,但成本昂贵,并导致政府财政问题及通胀出现。只有钢铁业,在取得首次高资助后,便达到国际竞争水平。
韩国的财政分配促成多个大型财团势力的扩张,受害
的是中小型企业。直至80年代,缺乏中小型企业无异有碍出口及总体增长,而且亦证明,要削弱大型财团的经济及政治力量,简直是异想天开。韩国政府未能发展一个具效率及竞争力的财政体系亦导致韩国企业只顾利用人口生产机械,而忽略了本地生产机械,从而防碍资本货物工业的发展。
韩国财政政策较台湾的抑压。台湾较次要及“非正式”的市场为中小型企业而设,而且台湾企业的发展较韩国的多元化。此外,台湾政策对外资较为开放。韩国大财团能成功地防止外国投资者竞争的同时,亦导致部分工业的技术发展相对疲弱。
韩国及台湾率先创立一个主要为外国企业提供相当于自由贸易基地的出口加工地区,让这些企业以国际价钱取得输入品。设于韩、台两国的出口加工地区的优势在于她们没有语言沟通、贪污,以及日本投资者在日本前殖民地所面对的政治问题。马山及,,,,,,,,,,东亚出口加工地区的创立地,运作得非常成功。(自,,年代中期起,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多个地区相比,成
绩尤为突出。)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大多数的干预主义行动只是表面功夫。汉城有一个“战争房”,墙上都布满了个别企业出口趋势显示板。而贸易部长及主要出口企业总裁均有直线电话,方便联系。
韩、台两国的成功,在某程度上可归功于两国的公共干预主义。由于两国忽略了政策中未革新元素所带来的歪曲现象,因而利用干预主义抵削这些现象是必须的。但同时,由于有关保护主义及管制的利益在,,及,,年代期间不断扩展,要透过紧缩保护及开放金融市场来改革两个经济,就显得难上加难。就将价格定为中位数而言,台湾便做得较韩国出色,原因是韩国仍维持她一贯的浓厚干预主义。韩国经济的相对脆弱性,以及政治不稳定,都是因为干预主义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
,,年代期间,马来西亚拥有强健的基本产品出口经济,但印尼及泰国,虽然农业资源相对丰富,却属全球贫穷国家。三个国家均采用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印尼在,,,,年后采用),奉行平衡预算案及严紧货币措施。如新加坡一样,泰国及马来西亚,在控制通胀方面非常成功。印尼及马来西亚纵然面对石油价格暴涨,在,,年代的宏观经济仍算稳定。
印马泰三国一直以输入替代品为主,但在保护输入替代品制造方面,则较,,年代的台湾及韩国,以及直至,,年代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弱。在泰国及印尼,走私令经济更加开放。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加上相对中立的贸易,不但加速了农业发展,而且促进,,年代的农业及矿物出口趋向多元化。,,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及泰国走向出口制造,以及本地及外国投资,包括香港及台湾。到,,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印尼加入泰国及马来西亚行列,成为出口劳动密集制造商。相对较小型的生产商占领先地位。
到,,年代,三个国家的保护主义者只着眼利益,致力增强保护及寻求其他形式的工业资助,从而促使对抗保护主义的政策的成立。包括撤销以数量计的进口限制。当时亦有引入贷款资助及免税期,但效力不大。寻求租金遂得到鼓励,但到,,年代期间,贸易政策改革亦能成功地在这三个国家推行。
由于非正式工业的经济机会不断增长,大大降低印尼(全球第三大发展中国家)、泰国及马来西亚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她们三国虽然离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与区内的菲律宾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发展进度已算不俗。
中国
中国是唯一一个中央策划,或前中央策划国家,于,,年代期间经济急剧增长。中国由经济停滞不前,至戏剧性的出现,要归功于两个工业。由集体耕作至个人耕作的农业生产复苏,促成经济改革。,,年代末期,食物短缺问题迫在眉睫,中国政府不单转向细规模的个人耕作,而且还更进一步减除对农业的误解。以往有意降低农业价格,再加上推行高度保护政策,目的是刺激工业化。虽然由国家经营的制造及服务行业运作欠善,令服务行业受到压迫,以至削弱了多重经济效益,但农业生产及农村收入却有急剧的上升。
出口亦担任一个关键的角色。由,,,,年至,,,,年的出口低微,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出口的增值零件(以国际价格)更低;换言之,生产众多出口的本地成本较从海外购买的高。出口货品差,市场推广恶劣,促使大部分货品经由香港转售。
当经济不景气迫使中国在,,,,年推行开放政策,五个获政府相当投资的特别经济区得以成立,当即成为“世界之窗”。这些经济区从外国注入高科技、与外资进行试验及从中国输出货物。到,,年代,,,个各自取得不同程度的中央投资基金及自由度的沿岸城市,亦成为特别经济区,自此而后,更多的特别区,包括海南岛及上海的浦东区,亦相继成立。这些特别经济区成立至今已有,,年。基于政治理由,他们全须被视为成功例子。纵然劳工流动在中国不获批准,但这些特别经济区吸引了大批劳动人口。此外,他们亦为本地企业及负责其运作的高干带来丰厚的财富。然而,成本收益分析显示,特别经济区浪费公共基金的程度足以令人诧异。而所选用的资本密集科技,不太适用于本地情况,原因是资金资助过高。另外,大多数情况是在海外流失兑换率。
自,,,,年,国家贸易公司在处理出口方面,获得的自由度更大。但他们仍然非从国企及其
分包商售卖货品不可。分包商运作效率往往较其母公司高。然而,这个行业的设计及品质恶劣、生产力低。大部分的企业,在,,年代早期有一定上升后,生产力又再次回落。他们的出口增值(以国际价格计)通常出现负数。
中国政府批准外国投资与国内企业进行合资企业,但有关情况却常变而含糊。决策要在多次延期后才可制订,而且多是专横跋扈。官方管治亦难以预测;实质劳工资金并非如想像那般低。特别经济区附加多项收费在工人(及其他生产要素)及工人方针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从而提高工人成本。,,年代期间,出口制造方面的正式外国投资继以低微。大多数外国投资均集中在旅游业,但投资者对中国方面有关的回报,从开始到现时为止都非常低。
由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密集生产商着手寻求工资低廉的地方生产,中国便开始其开放政策。虽然对来自香港及台湾的成功大型企业来说,在中国,尤其特别经济区及其他指定地点进行正式投资,无异是非常麻烦。但这些国家的小型企业家倒颇为愿意“非正式”方法,大多是正式与乡镇企业,或甚至(国家级及省级)国企谈判,与中国共同合作生产。与“正式”程序相比,这种“非正式”方法可让企业家更快进行生产。
在中国的运作情况是:原料从中国输入,而制成品以投资者可赚取利润的价钱向海外出售。从投资者彼此间的竞争可看出,在互不干预出入口产品价格以外的情况下,多余盈利是有限的。
部分设备是由投资者提供的。这些投资者着重劳动密集生产。他们引入计件工作及轮班工作,务求充分利用廉价实质工资成本。
输入的机械大多属二手贷。这些投资者亦参与管理、设计、检定及市场推广,而本地企业则负
责厂房及劳工供应。资金起初低廉,正反映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低,但随着技术及生产量上升,资金亦随即上扬。从中得益的不单只是工人们,还有负责谈判的高干及企业所驻扎的社区。珠江三角洲目前经济蓬勃,数个中国华南地区的情况亦然。部分本地企业家,包括私人,即所谓“合作”企业、村镇企业及一些国企,即使在没有海外中国伙伴的情况下,亦纷纷仿效,为本地市场及次要的出口市场生产。
在短短十年,中国已成为双重经济。中央政府的改革步伐仍然缓慢、集体拥有仍是共产党信仰宗旨、双重价格体系不断招来贪污。由于通胀压力,政府财政及金融政策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以收紧货币政策,因而造成“过热”现象。政府须从外汇赌博及其他价格转变,而并非从生产中赚取利润。当时经济欠缺了法律体系及组织发展,主要受损的就是资产净值。但经济仍能正常运作,原因是农业及出口市场讯息仍存在,而且私营拥有亦被默默地接受。至于新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会
否导致国家经济垮下,抑或在经济发展,尤其资产净值受损的情况下,双重经济能否屹立不倒,这些问题仍悬然未决。
菲律宾
菲律宾情况接近“拉丁美洲”模型,多于东亚模型。,,年代,菲律宾是东亚最先进国家,但至,,年代,便开始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与区内其他地区相反,农业不景气一直是菲律宾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年代的高保护政策导致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而政府未能征收公务员和大型机构员工以外的个人人息税,亦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企业税亦受到同样限制。浪费公共开支。一个镇压金融的高利润体系蓬勃起来。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未能稳定经济,导致通胀过高、还款出现危机、汇率过高,以及货币贬值。保护主义抵销,以及出口优惠,包括出口加工地区,这些方法都不见有效,“停一进”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尝试。它主张大量资助公共及私营向外贷款,这无异造成政府债台高筑。当时贪污猖狂。菲律宾的实质工资在,,年来停滞不前。唯有暂时及永久性的移民,可舒缓失业率及待业率不足的问题。
政府角色
由于东亚各政府试图将“日本模型”应用在国家发展上,歪曲了他们的角色,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造业及出口制造业增长上。然而,政府必须采取一个更实际的做法,包括考虑第一产业
(尤其农业)、二次产业及第三产业,务求刺激总体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稳定是东亚出口成功的基石。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在,,年代初期、印尼自,,,,年起,以及,,年代末期的台湾及,,年代早期的韩国,都是依赖税收,而并非借贷或加印货币来应付周期性及发展开支。公共开支大都是盈利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当预算赤字危机有可能爆发,预算将被大量削减。然而,菲律宾就是欠缺这分审慎。而通胀正是宏观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
区内各国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效率有异。由香港和新加坡,至另一端的区内其他国家,彼此的差距甚大。但除菲律宾外,区内各国的公共财政水平在经济增长初期甚高,又或随着国家发展,有关水平都有显著上升。具效率的财政策设施有助于货币政策集中处理稳定价格,即是维持低通胀率及将兑汇率置于均衡水平。经济增长迅速鼓励私人储蓄、有助于公共存款投资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及减低生产总成本。相对高的国内存款及投资是成功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指标。
金融政策方面,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具国际竞争性,而韩国的则属高度抑压体系。在韩国,由于政府借贷给私人企业时,进行详细的官方干预,导致经济大大失效。至于菲律宾,财政萧条歪曲生产架构,导致生产失效,以及为了非生产性目的,而向外国大量借贷。菲律宾的私人及公共借贷已达到“拉丁美洲”水平。
中立贸易政策
五个东亚模型显示了处理贸易政策的五种不同方法。
香港及新加坡的开放经济,再配合审慎的宏观政策,大大刺激两国出口增长。随着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及工资上升,再加上外资流入以及从世界各地审核新科技,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宏观经济稳定及中立贸易政策,不但鼓励各行业彼此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旅游业、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行业继而蓬勃增长),而且更促使海外投资。出口增长迅速及出口高比率(以个别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计)是主要行业,而并非增长的唯一来源。
这些国家中,具成效的公共干预大都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新加坡的经济干预政策存在着,,年代社会独立运作的意识形态根源。后来,为支持生产的经济自由,该意识形态渐被放弃,但残余的部分思想,仍有不同企业(公共及私营)不同地位的公务员奉行。他们善于利用税收及其他优惠作为与私人企业谈判的卖点。但这个迟来的财政改革(降低公司税及私有化)并未扰乱经济,原因是政府干预只是在跟随市场趋势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因此,所产生的浪费亦不致太大。从广泛涵义及大部分情况而言,
新加坡增长速度可媲美香港。新加坡的大量多余公共活动的主要成本,就是留住有为的新加坡人于共营机构,从而阻碍本土企业进化。
由于台湾及韩国在宏观经济改革期间没有走向中立贸易,当他们试图透过管制成立中立贸易,便须面对保护制造业的高成本。两国实施保护主义的措施有:数量入口限制(包括人口牌照)、提高关税、控制进军生产、生产配额、从抑压的金融体系实行借贷分配及控制价格。外国投资须受到监管,以防止外国公司剥削本地市场。
由适当政策引入,用来抵销歪曲成本的管制,导致更多额外的内联及互联行业歪曲、寻求租金及贪污情况出现。跟随的行政体系亦导致市场全面崩溃。要经济复苏,就必须加强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稳定及抗衡不适当的政策,亦有助加快进展速度。出口增长不但带来竞争力,而且亦令人们明白贸易及财政政策改革可取代昂贵的行政环境。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所行的发展方向与台湾及韩国的相同,但她们的天然资源更为丰富,走私猖獗,保护水平低,农业增长所受阻碍减少。石油价格暴升为印尼及马来西亚带来相当丰厚的资源,用在投资社会及实质基础设施上。但两国亦因未能维持保护政策,而浪费了部分石油租金,直至,,年代初期油价下降,在严竣压力下,政府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仍处于时间错位。宏观经济工具,尤其是有效及合理的税收仍有待建设。而货币及金融政策则欠缺一个架构基地。保护大都是数量性。到处都受到政府干预,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沉重。由
于目前农业及出口业的经济发展巩固,可望改革步伐能继续前行。
某程度上,成功的东亚模型似乎与菲律宾有些不同。菲律宾出现干预情况,究其原因是保护主义及抑压财政政策。政府试图采取抗衡措施对抗,但始终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跟随这个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无功而回,看来,菲律宾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主要相异之处在于菲律宾欠缺一个审慎的宏观经济。
后话
有关政府干预的讨论不只纯屑学术性质、,,,多个发展国家当中,只有少数展现急速、合理及可能维持的增长。对于大多数有待达到这个增长,对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研究出哪一个模式最适用于东亚极为重要。
问题
,、究竟何是成功因素:是日本模型所遵行的详细政府干预,还是稳定宏观经济及维持中立国际贸易,从而削减政府干预的开明政策,
,、为什么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显然是商机四现的淘金之地,
,、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东亚各国政府政治经济政策有何联系,
分析与提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急剧增长。十八世纪的英国,随着农业及工业革命的爆发,全国收入增长上扬,但到,,世纪及,,世纪上半期,平均每年实质全国收入增长率只有,,(非常少数国家,在极短时间及特别情况下除外)。大部分工业国在,,,,及,,年代增长迅速,每年实质人均国家收入增长达,,。发展中国家的成绩亦相距不远,这点倒令好几个研究其发展的经济学家惊讶。由,,,,至,,年,随着实质人均收入增长的人口增长只有,,。
日本追上先进生产水平的速度可算惊人,,,至,,年代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由,(,,增加至,(,,,其间甚至出现两位数字的增长。日本遂成为东亚“奇迹国家的先锋”。其他新兴工业国,如香港、韩国、新加坡及台湾亦随后赶上,而一些“接近”新兴工业国,如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的经济增长都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迅速,这点在,,及,,年代更为明显。东亚国家中,就只有菲律宾(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准则比较,表现亦算强劲)、越南、老挝及柬埔寨较为落后。
其实,其他地区亦有成功例子,只是增长迅速的东亚国家经济增长表现远远超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其实,部分东亚国家在,,年代的人均收入全球最低,但现在以人均收入计,他们已可与韩国、泰国及印尼等工业市场国家看齐。,,,,年,新加坡及香港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元,较爱尔兰或西班牙为高。
过去,,年,东亚国家的实质人均收入每,,年会增加一倍,但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自,,年代起,生活水平增加一倍的次数普遍只有一次。拉丁美洲的生活水平,于,,年代是发展中国家之首,但到,,及,,年代便停滞不前。有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撒哈拉非洲,生活水平自,,年代起便下降。
经济急剧增长可说是东亚国家的共同特性,虽然他们在,,年代期间的“起步情况”及发展水平、地理及人口情况,以至天然资源都有明显的差别。
与其他发展国家相比,无可否认东亚国家无论在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增长表现均非常出色。要量度贫穷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但对增长迅速的东亚国家而言,出色的增长表现明显地舒缓了贫穷情况。这点已被广泛传播,而且亦得到个别国家的估计支持。,,,,,,至,,,,年期间,活跃于贫穷的人口比例,由,,,跌至,,,。(有,,,属农村人口,,,是市区)。此外,保健及教育的实质指标亦显示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表现。
区内认为,经济进步并不是一个奇迹,而是一套致力于推动人民及其他资源,为迅速增长目标
努力政策所带来的成果。
毫无疑问,各政府在区内的经济发展所担当的角色固然关键,但对其角色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人认为政府直接干预可减少国内及全球市场“出错”机会,而他们“挑选赢家”及在其“工业哺乳”期以资助作为鼓励,对制造多元化比较优势有莫大贡献。成功介入经济,尤其工业发展的“日本模型”,被喻为是这些政府政策的根源。“日本”模型所采用的保护、市场管制、及以一连串的奖励来孕育新成立的进口取代品及出口工业,被视为成功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政府与商界在开发所谓“日本公司”概念上的紧密合作或甚至勾结,已成为主动工业政策的主要元素。他们相信凡有利于工业的,亦对经济有帮助。虽然有人就日本模型现况存有怀疑,但这个想法至目前仍屹立不倒。
对政府角色采取开明看法的人认为经济的成功应归功于中立及行政完善的政策。这些政策为消费者及生产商带来经济为主的价格讯号。开明经济学者认为财政、货币、金融、贸易及劳工政策的健全性,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持久性及公正。由于东亚经验似乎强调广泛的管制及“挑选赢家”,而并非鼓励增长或公平,造成了长期高经济成本及助长收入分配不平衡。与国内及国际市场缺点相比,政府干预是市场成败的更严重成因。干预政策所带来的恶果,现可见于日本经济由来而久的问题上。韩国无法抗衡其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行为。除香港及新加坡外,东亚国家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亦须面对与高成本公共企业、不会成长的新成立工业、以及因对农业及出口的偏见所带来的高成本,干预的好处亦令人难以放弃。过份的干预不但对经济造成破坏、政府腐败及不稳定,忽视社会贫困及环境退化亦会随之而来。而欠缺效率的经济往往削弱生活水平。
范文三:东亚经济奇迹的启示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里兹(Joseph E.Stiglitz)
经济译文 1997年10期
(译者前言:Joseph E.Stiglitz原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现已离校就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本文是世界银行对东亚奇迹和公共政策调研项目的论文的缩写)。
** *
东亚的经济奇迹引起众多疑问,为什么东亚这八个国家或地区(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泰国)能取得如此快的经济发展?是什么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仿效吗?东亚国家成功的一条共同经验是政府承担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
产业政策是用于指导开发和鼓励某些特定部门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采用它们?通过指导资源配置或广义而言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它们切实可行吗?
一、寻求何种政策?
大多数国家都有三个目标: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出口;建立国内生产系列中级产品的能力(如塑料和钢铁)。采用多种形式来支持特定的产业和进口必要的外国技术。首先,支持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教育——从而提供智力基础以便于技术的转移。其次,(通过金融市场管制)阻碍资本分配到诸如房地产领域决策意味着有高技术利益的领域可获得更多的资本的,如厂房和设备,第三,正如下文要讨论的,政府鼓励出口。第四,在一些产业,尤其是那些有众多企业的产业中,政府扶持技术发展方案,包括建立科研中心以提供服务——从鉴定新产品到为本身无条件的公司提供研究和开发。台湾和马来西亚为高科技产业建立了工业区,既让公司获得与该行业有关的原来分散的外部条件,也减少了准入的障碍(当一家公司的措施有益于多家公司——或能将成本转移到——许多公司而不仅仅是一家上游公司或下游公司,分散的外部条件将增加)。最后,政府还对其想支持的产业进行显性补贴和隐性补贴(通过低息贷款)。
扩大某些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不仅阻止了对外国投资产生厌恶的情绪,还通过提供合理的宏观经济管理、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由大量受过培训的工人组成的管理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来吸引资本流入。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都采取明显的步骤以确保,随着资本流入会有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转移。外国投资加快了扩张的步伐,减少因资本的可获得性、国内企业界和技术的有限所造成的约束。
二、为什么采用这种产业政策?
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是由于以下原因。理解这些市场失灵有助于解释这些政策之所以被采纳及它们如此有效的原因。
1.脆弱的及尚不存在的市场。在发展初期,市场往往不存在或运转不良,因此价格不能为资源配置提供好的信号。东亚的资本市场尤其脆弱,导致政府创建特殊机构吸收储蓄(邮政储蓄银行)和发放长期信贷(发展银行)。通过帮助建立证券与股票市场,政府也尽力发展金融基础设施。
增加了储蓄,政府必须决定如何分配这些资金。如果存在分配长期资本的建立完备的市场机构,政府便可以利用这些机构。而东亚国家没有,政府必须自行决定资源的分配,自然会将资金分配到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项目上。
2.技术溢出。私人市场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技术的生产和获取上,这主要是因为难以获得知识的收益。发展中国家通常运作于远低于工业国家的技术水平上;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是一个不断获取和改进现存技术的过程。专利保护确保卖者有权因新技术获取报酬,但不能为转让和改进现有技术的公司提供保护。采用和改进新技术包含着风险。如果成功会很快被效仿,公司便面临着“领先者输,随后者赢”的境地:由于竞争的压力,他们成功时获利很少;当他们失败时,便遭受损失。
3.营销溢出。另一种有价值的信息是关于营销的。知道哪里有某一产品的市场不是一条能保密的信息。如果一家公司花钱打听到美国人喜欢马德拉斯衬衫,那么这种衬衫的其他生产厂家也会利用这条信息。反过来是一国的产品树立了信誉。因此,日本产品高质量的信誉使所有日本厂商都受益。
这种营销的溢出效应引起政府用旨在优化国内产品的方案。(如香港用特种税收资助这些方案。在新加坡由权力庞大的经济发展委员会执行。)溢出效应还导致大批提高国家(地区)声望的方案的产生,这方面最显著的即是台湾最近鼓励本地公司获得商标认可的努力。
4.规模效益。这是一个有疑问的解释。并非前面所提的作为产业政策理论的所有论点具有说服力。在日本特别有影响的一个观点认为政府干预是使产业合理化所必需的。它表明没有政府的支持,公司规模会很小,且大量这种小公司会降低该部门所有公司盈利率(因此,日本政府不仅在60年代后期不指责钢铁业的高速集中,而且其最有名的错误之一是阻止本田——当时一家成功的摩托车制造商——进入汽车市场)。这种争论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如果规模确实能增大效益,那么一家公司可通过扩大产量而受益。这时其成本降低,进而能削弱其对手的竞争实力。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然的经济力量也会使产业合理化。
另一个稍有不同的坚持规模效益的观点也有些道理。增加的收益连同资本短缺会阻碍小公司的发展。他们不可能利用增加的收益来扩大,因为他们得不到资金或因为他们可获得资金的唯一渠道是贷款,而贷款风险太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可以降低资金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
增长的收益,尤其是在伴随资本市场不完善时,为战略性的贸易政策提供了依据。历史上,反对政府的贸易干涉的观点集中认为产业本身通过实践学习。如果现在的生产降低了未来的边际成本,那就产生了一种类似于静态增长收益的增长收益形式。一个扩大生产的公司能降低其未来产品的成本,并且降低其对手的竞争实力。幼稚工业论认为保护很重要,目的是年轻的公司能获得降低其生产成本的经验并付诸实施。对这一观点的批评认为,如果公司要从长远上赢利,就应承受现在可能发生的任何必要的损失。但这种假设的前提是资本市场完善。若资本市场不健全,一家公司承受不起这种损失,尽管它能使公司在最终可获得利的水平上生产。而且,如果公司不能尽其所能分配这些收益,那么生产所取得的社会收益将超过个人收益(Dasgupta和Stiglitz 1988)。此外,工业国家的大公司有可能乘机利用竞争不足,当人们认为提高价格就能增加收益时,竞争不足就很普遍。政府政策便指向于合理划拨这些租金(产生于主导竞争地位的超额利润)。
5.协调失灵。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普遍缺乏意味着价格不能执行它们的调节手段。因此政府在执行该职能时必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传统的例子是有关于下游行业和上游行业的发展:发展钢铁制造业得不到报偿,除非有相应的钢铁使用工业;同样,如果没有钢铁制造业,仅发展钢铁使用工业也无用。如果彼此等待,便毫无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政府在协调这两项活动中负有重要职能。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协调失灵在规模效益较大时尤为重要。例如,如果认为需要发展钢铁制造业,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型钢厂和一个大型钢铁使用行业。其他市场失灵,如缺乏市场风险机制,对这种失灵也有影响:高风险总伴随着这种大规模投资,而市场不能提供没有这些风险的机制。而且,没有单个的企业家能够独自积聚所需资本,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也意味着不能供应所需的资金,比起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具有承担某一单个部门巨额投资能力的组织,更不用说同时承担上游和下游企业投资的能力。因此协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重要,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更弱。
早期有关协调失灵的观点(Rosenshein-Rodan 1993和Murphy,shleiter Uishny1989)被直接批判为不具有说服力(Stiglitz 1994a)。这个问题可通过贸易轻易解决——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已由东亚国家设计出(并非得益于理论文献)。看来,仅通过进口钢材来发展钢铁使用产业,及通过出口钢材而不需要钢材使用业,来发展钢铁制造业是可能的。
在快速增长的早期,小产业也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绝大多数领域,对东亚国家经济腾飞负有责任——纺织、鞋类、运动商品和玩具,这些却并非规模经济或协调问题十分突出的领域。但是有一种更微妙的规模经济模式,其中政府的干预会起作用,而且影响这些领域的发展:大范围的,相当复杂的中级产品的可用性,能满足最终产品生产者的需要。但这些中级产品的销售商得不到产品的更大可用性所带来的所有收益。改进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双向的信息交流,使得中级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发展更加协调,是密切的利益。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进口中间产品不能作为国内生产的完美替代,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马来西亚,据说本地汽车制造商已为生产零部件的中级产品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溢出效应,而这些企业反过来又使其他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受益。
6.战略性谈判。在与其他国家或公司的谈判中,东亚政府常认识到,并利用市场环境的特点。讨价还价的结果依赖于双方的竞争实力。通过削弱技术购买者之间的竞争和尽力增强销售者之间的竞争,政府成功地调拨了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更多的盈余,不这样的话,更多的盈余会被扣留。如在日本,某单个公司有时被授权商议许可证协议;它将被迫同行业中其他公司共享这项技术。
四、这些政策起作用吗?
产业政策一直到广泛的批评,根据是(有些甚至自相矛盾)它们是无效的或扭曲的。第一种批评认为产业政策空洞而不具体。批评者引用了统计数据,如发展银行发放贷款的小额比例。然而这些统计数据不具有说服力:如日本工业银行的贷款结果比实际贷出的美元大得多,原因是它的指示性或风险共享效果(Stiglitz,1996)。政府扩大公司股份的政策通过杠杆作用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工具能用于影响产业政策。正是所有这些工具累积的结果在起作用。批评更宜指向那些建议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完全控制资源分配的人。这种设想有两方面错误。第一,公司在做大部分资源分配的决策时——肯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但并不直接受其控制。没有一个东亚国家是集权控制型的经济。第二,认为政府自身做决策的观点看来是误导。工商业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是广泛的(同时许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即政府前任官员)。
然而,对于产业政策是扭曲的指控应多加考虑。纵然政府干预有理论依据,这个观点宣称政府在挑选赢家上未做好工作。政府的错误实例常被引以为据。有些例子表明政府妨碍了公司发展,例如本田回头看,这明显不应该;另一些例子中,政府鼓励了一些产业的发展(如石化产业)现在来看这可能不对。
对于这类批评有四类答复。首先,由政府做的英明决策不可避免包括错误:一项仅支持确定无疑的赢家的政策才可能无风险。相对少的错误则说明政府挑选赢家的能力。第二,政府并不是重权控制。虽然它会犯判断失误,但不会将观点强加到其它愿意拿自己的资本冒险的企业上。这是分权决策的一个作用:它保证了错误观点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在很大的程度上,政府政策并非在狭隘的概念中来选择赢家。好几个政府部门决定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在一定意义上,那是在选择一项成功的发展战略,但没有微观管理的义务。甚至当政府明确了支持哪个产业,银行也有权决定支持发展该产业的哪家公司或哪个项目。
第四,产业政策的重点与其说集中在选择赢家上,不如说是鉴别市场的失灵—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利用大量潜在的溢出效应。考虑这样的溢出效应有助于解释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的行业。培训也是一个例证。公司能从培训过的劳动力身上受益,但由于一旦接受了培训,工人可能跳槽,去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公司进行培训的动力因此不足。然而有技能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通过将重视教育来承担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义务。
而且,批评产业政策是选择赢家的误导的观点忽视了政府行为更大的范围,如它在某些制造业发展中的先锋作用。“选择赢家”似乎是从一大堆申请者中挑选出长期社会效益最大的那些。东亚政府也执行着企业管理性的职能。企业家素质要求结合技术及营销知识,对未来的预见、承担风险的意愿及筹措资本的能力。在发展的早期,这些因素尤其缺乏。东亚政府便插入以填补空白——目的是为了促进而不是阻碍私营企业的发展。
政府也有效地对其支持的接受者进行监管,并保证他们不会将资金抽走用于私人用途。其他的政府政策,如导致更多股份融资的那些,减少了监管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如增加银行业体系的稳定性,可使金融监管更加有效。
单项政策不能确保成功,成功的政策中包含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东亚的奇迹更主要是政治因素造成。政府采取各种动力和管理机制来提高公共机关的效率,减少腐败性。而且由于大家对错误的认识提高了适应性和反应能力,这是持续成功的最终基础。
译自《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员》96年8月刊
曹岚译
作者介绍:(美)约瑟夫·E·斯蒂格里兹(Joseph E.Stiglitz)著
范文四: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
中国网?? 时间: 2006-10-12
(一)东亚的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地的束缚,走向政治独立,寻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东亚地区的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经过40年之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询它背后的故事。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1913~195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在2.21%左右;从1950~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9%;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1973~1998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1%(Maddison,2001)。图7-2中给出的日本人均收入也显示了相同的增长态势。在6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长强劲,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4%左右。70年代之后,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在90年代经济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在2%以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而且也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率。
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时间上比日本晚10年左右。从1960~2000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年平均分别为5.8%、6.3%、5.6%、6.4%(见表7-2)。在这40年时间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在6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7.11%。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都是在7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分别达到7.70%、7.84%。韩国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6.52%。经过大约40年的经济增长,“四小龙”相继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不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四小龙”的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以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为参照对象,图7-2显示了1960~2004年日本和“四小龙”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
东亚经济增长不仅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都有明显进步。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了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等众多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总体福利状况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越大,说明它的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越好。
1975年,日本的经济起飞已经完成,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伴随着经济增长,日本的社会事业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75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57,与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0.867)非常接近。此后,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上表现出相似的上升速度。到2003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升到0.943,美国则为0.944,两者基本一致。同样,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也有显著提高。1975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707、0.725和0.761;到2003年,它们分别上升到0.901、0.916和0.916,比1975年提高了0.194、0.191和0.155,而同期的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上升0.086、0.077。这样,通过成功的经济追赶,日本和“四小龙”与美国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趋同化的态势。
(二)是什么创造了“东亚奇迹”
在Solow(1956)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物质资本增长由外生的利率变量决定,劳动力数量增长由外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决定,因此,物质资本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在长期都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当经济增长过渡到稳态均衡之后,人均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这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
如果把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那么,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后来,内生增长模型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归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也是由人力资本回报的外生变量决定,那么,扣除人力资本之后的剩余部分,即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惟一因素。
尽管同样是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东亚奇迹”,但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Young(1994)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从1966~1990年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要素积累。在此期间,“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随着部门间劳动力重新配置,非农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1.5~2倍。在25年中,“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3%~4%。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OECD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
Krugman(1994)认为,神话般的亚洲奇迹只不过来自高投入的经济增长。这种神话与前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地相似。前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推动了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是当时美国经济的3倍。当时,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虽然批评前苏联经济数据有夸大成分,但也承认其增长的事实。美国经济学家凯尔文?胡佛甚至得出“一个集体主义的独裁式政府在本质上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式政府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他还预测前苏联经济将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超过美国。Krugman用前苏联作为例子类比,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他还进一步将“四小龙”与日本做比较。他认为,日本在技术创新上接近美国,技术进步在日本经济增长中有很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四小龙”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种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Bhagwati(1996)认为,“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四小龙”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投资率都非常高,并持续了20~30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Krugman认为“四小龙”没有技术进步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追赶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如果把东亚经济增长按照每1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进步上是递增的。同时,Krugman对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Desai(1990)的研究,缺乏有效激励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是前苏联计划经济走向崩溃的原因,而不是来自边际报酬递减所带来的投资下降。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魔术”。选择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出口增长、国际竞争、FDI流入、人力资源开发等因素,不仅刺激了国内投资,而且也推动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
World Bank(1993)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能够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经济获得成功没有任何“奇迹”而言。但是,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于它们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东亚奇迹”的实质是不仅有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东亚奇迹”中的人口因素
无独有偶,东亚经济起飞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迅速转变阶段。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Mason, 1997)。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来自人口因素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老龄化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出生率迅速下降意味着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进入了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时期。二是日本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三是日本狠抓国民素质,使日本在一代人的成长期间有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
为了配合社会经济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日本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由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培养通常需要10~20年时间,日本还兴起了大企业培训工人制度,以确保企业留住人才。在农村还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的能力。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既满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大量劳动力供给的需求,也通过人力资源积累来实现科技创新,从而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亚洲“四小龙”的相似发展经验,也证明了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关联。1961年,韩国把家庭计划确立为一项国策,并把人口控制目标规划纳入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家庭计划政策实施,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带来了总抚养比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1995年的41.4%,从而开启了韩国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见图7-3)。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1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时间和经济起飞时间比韩国稍早,但比日本稍晚。台湾人口抚养比呈现两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张喻婷、陈信木,2005)。在1950~1965年间,幼年抚养人口数量快速扩张带来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在1962年达到最高点94.1%。1960年代中期之后,人口抚养比的压力减缓,抚养比不断下降,到1995年下降到45.8%。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见图7-3)。在人口转变的同时,台湾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如从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这些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创造了重要条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出来的“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口转变(Bloom and Williamson,1997)。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亚经济由过去的人口负担阶段(burden phase)过渡到人口馈赠阶段(gift phase),这个过程大约有50年左右的时间。一般而言,东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平均为2.6%;但是,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估算,东亚经济在1966~1990年人均GDP 6%~7%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大约为1.4~1.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的1/3(Bloom and Williamson,1997)。
Bloom and Williamson(1997)还比较了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非洲、欧洲、南美、北美、大洋洲等不同区域人口转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这种趋异性能够较大程度地解释洲际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由于人口转变呈现出时间上的序列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东亚收获人口红利的时间早于东南亚,而东南亚又早于南亚。
(四)“东亚奇迹”中的政府角色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一次性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经济发展将有可能失去实现起飞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会为人口负债背上沉重负担。能否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政策措施。总体而言,日本和“四小龙”都是通过制定和运用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
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日本和“四小龙”在起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相比日本,“四小龙”出口导向特征非常显著。从图7-4可见,伴随经济起飞,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的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1~3倍。
出口导向战略在本质上是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这种战略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代的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Leff,1969;Mason,1997)。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打破了低水平的发展陷阱,踏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图7-5展示了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惟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五)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在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经济学家眼中,人口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代名词,人口数量增长结果会带来食品消费短缺问题和环境资源压力问题。所谓环境资源压力只不过是食品消费短缺问题的现代翻版。这种绝对的人口数量观不仅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且忽略了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可以把人口从简单的消费者转变为同时也是生产者,激发人类发明创造的潜能,推进技术进步,从而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在人口、自然和环境之间形成和谐关系。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我们树立新的人口观提供了一个现实支撑。
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贡献作用并不是天赐禀赋,可以自动地获取。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是一次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经济起飞,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促进市场发展和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收获人口红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有人口红利期,就会有人口负债期。当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快,而“四小龙”的未来老龄化速度比日本还快。日本人口老龄化冲击对劳动供给、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等的影响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和财政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总和生育率急速下降,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整个社会迅速老化,劳动供给短缺诱发的劳动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由于各自的人口转变起点时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体制和政策、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它们收获人口红利的时间终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四小龙”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而日本收获人口红利阶段已经结束,需要担负起老龄化社会的养老负担。
目前,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195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只有4.9%。伴随着经济起飞,日本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只用了20年时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年,老龄化率上升到7.1%。目前,日本老龄化率接近20%,相当于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从趋势上看,未来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到2020年,大约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到2040年,大约每3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见图7-6)。亚洲“四小龙”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结果带来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到205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接近甚至超过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减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例如,日本的人口负担系数在1970年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之后,人口负担系数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给日本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人口老龄化所支付的社会负担急剧上升。人口结构老化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
首先,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抚养比,减少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这相当于增加了对他们征收的收入税,因此,削弱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意愿,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数量。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Pench(2000)认为,老年抚养比只是一个人口学定义,它没有考虑真正提供收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是老年经济抚养比,它是指被抚养老年人口数量相当于所有就业人口的比例。如果考虑经济抚养比,那么,人口老龄化状况更加严重。例如,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影响大约为0.5个百分点(Pench,2000)。
其次,现收现付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私人储蓄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同时,人口结构老化之后,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Yamada and Yamada,1988)。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这种危机进一步诱发了经济增长问题。
再次,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日本劳动力市场非常僵硬(如终生雇佣制度),技术创新不足,储蓄减少和劳动供给下降,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资本市场不健全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的,人口老龄化是这些问题的内在诱因,“旧思维和旧行为的老化日本,是日本政治危机的症结”。日本能否度过这个危机,关键看日本如何改革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为日本经济摆脱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王德文 蔡昉)
范文五:东亚奇迹启示中国复兴
华生?2014-03-13 星期四
为什么东亚五个经济体,特别是同为从农业社会转化而来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做到了?它们抓住了什么不为人关注而又至为关键的链条呢?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我们人均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相近的东亚成功现代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指出,“从1950年以来,超过100万居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香港、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升到高收入行列。”
即除了沙特阿拉伯这个特殊的产油国之外,二战后实现了从低收入直接跨越进高收入的就只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
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25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增长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13个,其中除了马耳他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欧洲地中海旅游岛也刚达到高收入门槛外,只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长为真正的高收入经济体。从这个被称为战后奇迹的东亚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赖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这样有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从而就具备了追赶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二,除新加坡、中国香港为城市经济体,无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由于各自的特殊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较为平均,为其后的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与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没有或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相当不同。
第三,虽然这五个经济体均非典型的欧美民主体制模式(日本战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期间,是在民主外壳下的自民党55年一党执政体制;韩国在转型期是军政府统治;中国台湾是蒋家父子威权统治;新加坡当时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民主外壳下的威权统治。中国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统治),但均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政府均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了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提供了经济追赶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
这与同为中等收入的中东地区国家战乱不断、社会不稳,以及拉美地区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大幅摇摆、恶性通货膨胀不断等形成鲜明对照。韩国、中国台湾还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前后较为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为后续持续增长提供了避免社会对抗的政治结构。
第四,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战后均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表),并以可融入的市民化奇迹般地避免了历史上早期工业化国家和现代拉美地区及南亚地区国家的普遍贫民窟现象。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大都市经济体则通过政府超大规模地提供基本国民住宅的办法,也避免了城市贫民窟。[1]这样东亚经济体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很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大,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从而实现了国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这样人的城市化市民化就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据来源:日本数据来源于日本内阁府统计局,《国势调查报告》,昭和30年(1960),昭和40年(1965),昭和55年(1980)《府县分类人口与人口密度》;韩国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计划院统计局;台湾地区1960年数据来源于台湾逢甲大学都市计划系,刘曜华,2004年《台湾都市发展史》,1973年以后数据来源于行政院经建会住宅及都市发展处编印《都市及区域发展统计汇编》。
注:相比之下,中国从1991年27.35%的城市化率起步,至2012年的22年间,名义城市化率仅达到52.7%,实际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35%左右,明显还属于城市化的前中期。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典型的城乡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转型过程中,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始终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而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包容性增长。
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两个完全没有自然资源的孤立城市,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和资源以立足,长期实行低税政策,再分配调节力度明显弱于非孤立城市的正常国家和地区,因而基尼系数较高,但仍与拉美国家的高度两极分化不能相提并论。
图:中国香港、新加坡及拉美四国基尼系数情况对比
综合以上五条,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五个东亚经济体所做到的,恰恰是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标题,即可持续增长与包容式发展。因为可持续增长才能实现追赶以不断缩小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包容性发展则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内生增长理论揭示,当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人力资本与无形资本的时候,人的普遍素质就越来越扮演中心的角色。
这就需要给予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他们的后代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能够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造致富。这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社会转型的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就意味着要能在大大减少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发展规模经济的现代农业,同时又能保证农村转移人口能够普遍就业、住有所居和融入城市,平等地享受市民权利。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又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那么,为什么东亚五个经济体,特别是同为从农业社会转化而来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做到了?它们抓住了什么不为人关注、而又对成功转型至为关键的链条呢?
东亚经验的第一条,即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恰恰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做的事,也是中国这30多年来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
不过,正如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总结的,坚守这些新古典理论的建议对于增长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赶上发达国家。因为二战以后,搞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多,但成功现代化的却是凤毛麟角。
东亚经验的第二条,也是我国做的最成功之处。我国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虽然过于激进,但属于最彻底的均分土地的改革则无疑。
在经过后来集体化的曲折和弯路之后,80年代初的家庭土地承包是一场最公平的均分土地运动,对于后来农产品供给的丰裕、农民逐步从土地上解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
经验的第三条,即有效和有为的政府,一方面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另一方面提供经济追赶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应当说也正是中国的强项和过去的成功之处。今后需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们公民意识的增长,国家如何与时俱进地推进法治化和民主化。
东亚经验的第四条,应当说恰恰是我们的短处。由于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废除和进行根本改革,中国的城市化长期以来走了一条农民进城离乡不离土的道路,就是农民进城武务工之后,仍然不改变农民身份和保有家乡的土地,城市户籍也不对其开放。
这样往往是农民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又返乡种田。这种低成本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帮助中国以成本优势成为世界工厂。这也是至今很多人仍然对这个模式念念不舍的原因。
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不准备返乡,农民工的两栖生存方式既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巨大浪费更造成农民工及其后代的素质无法提高,同时也影响了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事实上已经走不下去。
外出务工人员的流民化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可融入的城市化市民化,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最紧迫的挑战。
东亚经验的第五条,更是我们的软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分布状况变成世界主要大国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不考虑巨大隐性收入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接近0.5的危险水平。
中国以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在是世界上排名在近百位的水平,已经开始消费世界上近一半的奢侈品。全球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能平稳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内部的剧烈冲突、社会动荡和经济折腾,这显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特别是借鉴他们成功经验的后两条,对于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和民族复兴,显然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1] 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新加坡居住在政府租屋(HDB)的人口比重为82%,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香港有46.2%的人口居住在公营永久性房屋。资源来源:新加坡统计局《HDB Annual Report 2008/2009》,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统计数字2012》。
作者华生,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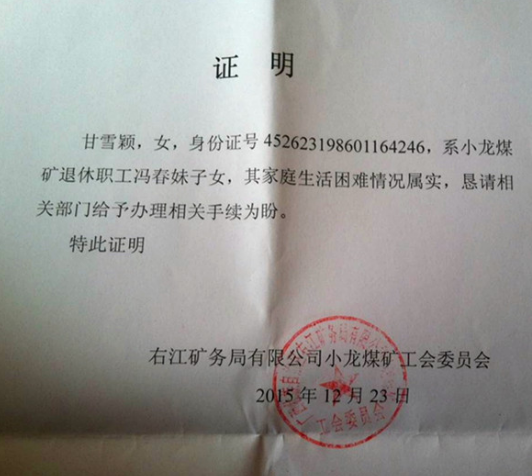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