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一:老舍的故事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小孩子打洋人的故事,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喜欢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激情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第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力量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
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鼓励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发国难财,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这时期有最着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但是,1962年开始的**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共产党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范文二:老舍:听来的故事
宋伯公是个可爱的人。他的可爱由于互相关联的两点:他热心交友,舍己从人;朋友托给他的事,他都当作自己的事那样给办理;他永远不怕多受累。因为这个,他的经验所以比一般人的都丰富,他有许多可听的故事。大家爱他的忠诚,也爱他的故事。找他帮忙也好,找他闲谈也好,他总是使人满意的。
对于青岛的樱花,我久已听人讲究过;既然今年有看着的机会,一定不去未免显着自己太别扭;虽然我经验过的对风景名胜和类似樱花这路玩艺的失望使我并不十分热心。太阳刚给嫩树叶油上一层绿银光,我就动身向公园走去,心里说:早点走,省得把看花的精神移到看人上去。这个主意果然不错,树下应景而设的果摊茶桌,还都没摆好呢,差不多除了几位在那儿打扫甘蔗渣子、橘皮和昨天游客们所遗下的一切七零八碎的清道夫,就只有我自己。我在那条樱花路上来回蹓跶,远观近玩的细细的看了一番樱花。
樱花说不上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它艳丽不如桃花,玲珑不如海棠,清素不如梨花,简直没有什么香味。它的好处在乎“盛”:每一丛有十多朵,每一枝有许多丛;再加上一株挨着一株,看过去是一团团的白雪,微染着朝阳在雪上映出的一点浅粉。来一阵微风,樱树没有海棠那样的轻动多姿,而是整团的雪全体摆动;隔着松墙看过去,不见树身,只见一片雪海轻移,倒还不错。设若有下判断的必要,我只能说樱花的好处是使人痛快,它多、它白、它亮,它使人觉得春忽然发了疯,若是以一朵或一株而论,我简直不能给它六十分以上。
无论怎说吧,我算是看过了樱花。不算冤,可也不想再看,就带着这点心情我由花径中往回走,朝阳射着我的背。走到了梅花路的路头,我疑惑我的眼是有了毛病:迎面来的是宋伯公!这个忙人会有工夫来看樱花!
不是他是谁呢,他从远远的就“嘿喽”,一直“嘿喽”到握着我的手。他的脸朝着太阳,亮得和春光一样。“嘿喽,嘿喽,”他想不起说什么,只就着舌头的便利又补上这么两下。
“你也来看花?”我笑着问。
“可就是,我也来看花!”他松了我的手。
“算了吧,跟我回家溜溜舌头去好不好?”我愿意听他瞎扯,所以不管他怎样热心看花了。
“总得看一下,大老远来的;看一眼,我跟你回家,有工夫;今天我们的头儿逛劳山去,我也放了自己一天的假。”他的眼向樱花那边望了望,表示非去看看不可的样子。我只好陪他再走一遭了。他的看花法和我的大不相同了。在他的眼中,每棵树都象人似的,有历史,有个性,还有名字:“看那棵‘小歪脖’,今年也长了本事;嘿!看这位‘老太太’,居然大卖力气;去年,去年,她才开了,哼,二十来朵花吧!嘿喽!”他立在一棵细高的樱树前面:“‘小旗杆’,这不行呀,净往云彩里钻,不别枝子!不行,我不看电线杆子,告诉你!”然后他转向我来:“去年,它就这么细高,今年还这样,没办法!”
“它们都是你的朋友?”我笑了。
宋伯公也笑了:“哼,那边的那一片,几时栽的,哪棵是补种的,我都知道。”
看一下!他看了一点多钟!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对这些树感到这样的兴趣。连树干上抹着的白灰,他都得摸一摸,有一片话。诚然,他讲说什么都有趣;可是我对树木本身既没他那样的热诚,所以他的话也就打不到我的心里去。我希望他说些别的。我也看出来,假如我不把他拉走,他是满可以把我说得变成一棵树,一声不出的听他说个三天五天的。
我把他硬扯到家中来。我允许给他打酒买菜;他接收了我的贿赂。他忘了樱花,可是我并想不起一定的事儿来说。瞎扯了半天,我提到孟智辰来。他马上接了过去:“提起孟智辰来,那天你见他的经过如何?”
我并不很认识这个孟先生——或者应说孟秘书长——我前几天见过他一面,还是由宋伯公介绍的。我不是要见孟先生,而是必须见孟秘书长;我有件非秘书长不办的事情。“我见着了他,”我说,“跟你告诉我的一点也不差:四棱子脑袋;牙和眼睛老预备着发笑唯恐笑晚了;脸上的神气明明宣布着:我什么也记不住,只能陪你笑一笑。”“是不是?”宋伯公有点得意他形容人的本事。“可是,对那件事他怎么说?”
“他,他没办法。”
“什么?又没办法?这小子又要升官了!”宋伯公咬上嘴唇,象是想着点什么。
“没办法就又要升官了?”我有点惊异。
“你看,我这儿不是想哪吗?”
我不敢再紧问了,他要说一件事就要说完全了,我必须忍耐的等他想。虽然我的惊异使我想马上问他许多问题,可是我不敢开口;“凭他那个神气,怎能当上秘书长?”这句最先来到嘴边上的,我也咽下去。
我忍耐的等着他,好象避雨的时候渴望黑云裂开一点那样。不久——虽然我觉得仿佛很久——他的眼球里透出点笑光来,我知道他是预备好了。
“哼!”他出了声:“够写篇小说的!”
“说吧,下午请你看电影!”
“值得看三次电影的,真的!”宋伯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的价值:“你知道,孟秘书长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一点不瞎吹!同系同班,真正的同学。那时候,他就是个重要人物:学生会的会长呀,作各种代表呀,都是他。”
“这家伙有两下子?”我问。
“有两下子?连半下子也没有!”
“因为——”
“因为他连半下子没有,所以大家得举他。明白了吧?”“大家争会长争得不可开交,”我猜想着:“所以让给他作,是不是?”
范文三:老舍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舍鲜为人知的故事
险些死于洋刀
老舍出身于北京一个满族贫困家庭。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父亲在巷战中受伤,爬近家门时死了,当时老舍1岁。老舍长女舒济说,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冲进了老舍家,捅死大黄狗。炕上有两个大箱子,被他们翻得底朝天,箱子正巧扣在熟睡的老舍身上,使他躲过一劫,死里逃生。
感念恩人
在老舍的记忆中,母亲的手永远是红肿的。父亲死后,母亲靠帮人家缝洗和当佣工,将老舍带大。一天,大槐树底下来了个刘大叔,他见老舍六七岁了,就帮助他上学。老舍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刘大叔后来出家,法号为宗月大师。
老汉撂倒小伙
老舍是八旗子弟,能文能武,说学逗唱样样行。上世纪30年代,他从济南搬到青岛住,写作累了,就练拳脚。诗人臧克家来老舍家探望他,一进门吓了一跳,墙上挂满了刀枪棍棒。臧克家问:“这怎么搞的,”老舍说:“我在锻炼身体。”
1964年,老舍率中国作家团去日本访问。有一日本青年听说老舍是习武之人,向他请教武艺。65岁的老舍婉拒不得,只能接招。没几个回合,小伙子被撂倒在地,众人皆惊。没想到拄着拐杖的文人老舍竟然还有这般力量。
买画物归原主
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北大荒,与亲朋几乎断绝来往,只有新凤霞的书信给他带来一点温暖。吴祖光说:“老舍先生经常问起我,并叫凤霞多给我写信。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多写,一天写一篇,说是让祖光看了高兴。这使我成了收到家信最多的人。”
1960年初,吴祖光和新凤霞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迎面遇见老舍。老舍把两人请到家里,拿出一幅画。吴祖光愣住了,这是齐白石给他画的一幅《玉兰花》,家境困难时新凤霞卖给了画店,竟被老舍买回来了。吴祖光含泪说:“请先生在画上写几个字吧~”老舍写的是:“某年某月在画店购得此画,今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至于买画花了多少钱,老舍说:“不用问啦。对不起你的是,我没能力把凤霞卖掉的画全给买回来。”
摘自《新民晚报》2010年4月12日
范文四:老舍的小故事
老舍的小故事
19岁当小学校长
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最伟大的字——饭”
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希望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朋友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写着玩”写出的大师
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老舍如何写《四世同堂》
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老舍还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老舍三岁那年,就没了父亲,母亲靠给穷人洗臭袜子养活他。到九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一位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了他,老舍上学了,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刘大叔是有钱人,也是大善人。他办贫儿学校、粥厂、慈善事业,把钱多多施出去。后来出家为僧,人称宗月大师。坐化后,烧出许多舍利子。刘大叔以肉身实践了“死而富有是可耻的”这一句几十年后才被人说起的话。
宗月有个女儿,小时候,老舍常去刘家玩,爱上了她。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个小儿女说过一句两句没有意思而甜美的话、富小姐和胡同串子,身份差太远,婚嫁谈不上。但知道她没有定亲,令他安心。
后来老舍出了国,刘小姐随父出家为尼。过了好些年,老舍回国了,刘小姐成了暗娼。其间,发生了什么?无从推测。可能那尼庵本来就不干净,刘小姐错入了虎口;也或她是“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总之,一个黄花大闺女,想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哪儿那么容易。全世界都是嘿嘿冷笑的恶势力。 他千辛万苦找到她。她剪了发,脸上有很多粉和油,洗净了大概像一个病中的产妇。她始终不正眼看他,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应当有吗?
他还爱她,但这爱成了苦酒,折磨他。他们原本本不当户不对,现在更加如此,只是高低掉了个儿。朋友看出他的悲苦来,没直说,假装闹着玩地暗刺他,意思是,她不配他。 她不配?她本来不是大小姐吗?她沦为赤贫,不也因为她父亲的慷慨施舍吗?而老舍,其实也是受益人之一呀。不过,给是自愿的,得到的人,不欠她们家。反之,如果邀恩图报,那她就是无赖小人,受者更加心安理得。这叫什么道理?但这确实是道理。
老舍没娶刘小姐——是他想娶而刘小姐不肯,还是他根本没打算娶?再爱她,大概也不能把一个暗门子用大花轿接回家去。我们很难知道真相了,他的记忆被打散了,放在他的小说里、散文里。一幅最美的画,碎纸机里走一遭,也就全是纸屑,什么也拼不出来。老舍34岁,才在朋友劝告下结了婚。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走这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微神,一个没有故事的主题。 老舍老在提海棠花,“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大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死后但愿葬在海棠树下,或着。。。。。。他什么也做不了!
最后老舍还是与胡絜青结婚了~
老舍与**
范文五:作家老舍的成长故事
作家老舍的成长故事
导语: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下面是小编精心收集的名人故事,希望能帮助到你!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一一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
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棗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做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
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
他每日一餐,人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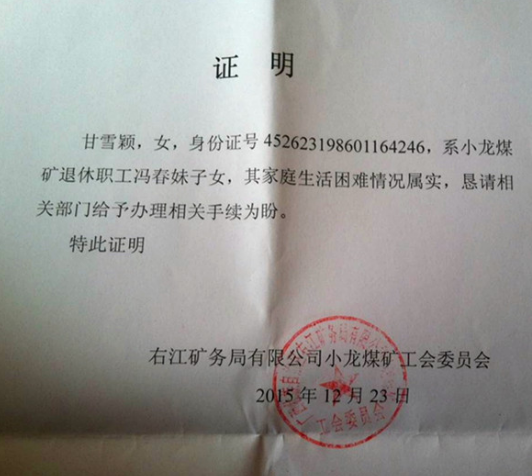

 z楠宝
z楠宝

